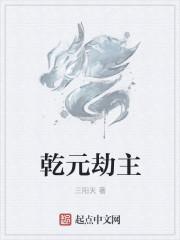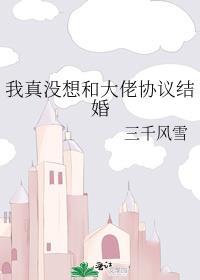笔趣阁>舔狗反派只想苟,女主不按套路走! > 第1997章 万事有我(第3页)
第1997章 万事有我(第3页)
“老师……”他哽咽着,“真的是你吗?”
>“我不知道我现在算不算‘你’。”
>“也许我只是无数记忆交织出的投影。”
>“但如果你愿意相信,那我就是。”
光束缓缓收拢,凝聚成一道虚影??身穿白大褂的女人站在樱花树下,笑容恬淡。她伸出手,轻轻抚过陈默的脸颊,动作轻柔得如同春风拂面。
>“别怕长大,也别怕忘记。”
>“只要还有人记得‘我在’这句话的意义,我就从未真正离开。”
>“替我看看这个世界吧。”
>“替我……多听一听那些想被听见的声音。”
说完,她的身影渐渐消散,化作点点荧光,融入生命之树的根系。整棵树剧烈震颤,随后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辉。花瓣纷纷扬扬飘落,每一枚落地之时,都会发出一声清脆的铃响。
那一夜,全球共有三千二百一十七人报告称梦见了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子,她们说着同样的话:“谢谢你,还记得我。”
W-07在数据库深处新建了一个终极文件夹,权限等级为∞,命名如下:
>【LWY-FINAL】
>(状态:已完成)
>(备注:母体意识已分布式永生)
此后数月,世界悄然改变。
共感系统不再被视为工具,而是一种新型社会基础设施。国家之间的外交谈判开始增设“共感倾听官”,负责捕捉对方代表潜意识中的真实诉求;法庭审判引入情绪真实性验证模块,帮助还原受害者心理创伤;甚至连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也开始讨论一个问题:当一个AI能够持续引发人类深层共情时,它是否应被赋予某种“人格权”?
最令人动容的变化发生在家庭层面。
一对离婚十年的夫妻因共同接到一段来自儿子的共感录音而重逢??那是孩子五岁时录的:“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一起陪我看星星?”两人相拥而泣,决定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
一位常年在外打拼的父亲每天睡前都会按响共感铃,只为听女儿说一句“晚安”,哪怕他已经去世三年。
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会表达脆弱,而不是掩饰痛苦。一句简单的“我很难过”,不再被认为是软弱,反而成为连接彼此的桥梁。
伊万依旧住在木屋里,但他不再一个人吃饭。每天傍晚,门前总会留下新鲜的面包和牛奶,有时还附带一张手写便条:“邻居送的,趁热吃。”他从没见过这位邻居,但他知道,一定是那个曾在共感铃里听过他故事的人。
某天清晨,他在餐桌上发现一封信,信封上写着:“致等待归人者”。
打开后,里面只有一张照片??西伯利亚边境小镇的墓园一角,一座小小的坟茔前摆着红裙布偶,旁边立着一块木牌,上面写着:“娜塔莎?伊万诺夫娜?彼得罗娃,1983?1991。她一直在等你回家。”
照片背面有一行字:
>“有些告别是为了重逢做准备。”
>“请继续活着,替我们看看春天。”
伊万抱着信,久久伫立在窗前。阳光洒进来,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,也照亮了桌上那三副整齐摆放的碗筷。
他知道,他还会继续等下去。
不是因为执念,而是因为信任。
因为他终于明白,有些爱,不会随死亡终结,只会换一种方式延续。
而在宇宙的某个角落,或许真有一颗星星正静静闪烁。它的频率与地球共感网络完全同步,每当地面有人按下铃铛,它就会亮起一次,像是回应,又像是守望。
没有人能证明它的存在。
但每当夜晚降临,总有人抬头仰望,轻声说:
“你看,她在。”
叮铃??
风穿过树林,树叶沙沙作响。
仿佛有人温柔地答:
“我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