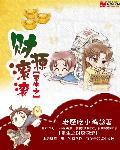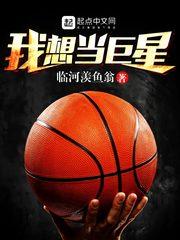笔趣阁>贫道略通拳脚 > 第一千八百零六章 何止九道(第1页)
第一千八百零六章 何止九道(第1页)
李言初的武道修炼起来更快。
他的武道并非包罗万象,而是走最简单最直接的道路,以力证道。
这种简单粗暴的证道方式虽然缺少变化,可是好处也十分明显,
那就是快。
李言初以最短的时间。。。
黄沙如海,风卷残云。
陈小满与阿元踏入西漠时,正值旱魃为虐,百里无水。天地间只有一条枯河蜿蜒而过,河床裂开如龟背,仿佛大地也在干渴中呻吟。远处佛窟群依山而凿,层层叠叠嵌在赤岩之上,宛如巨兽张口,静候迷途者入腹。
他们一路打听“七灯照冥图”,却无人知晓。唯有牧羊老翁眯眼遥指最深处那座被流沙半掩的洞窟:“那是‘哑窟’,三十年前有个疯和尚住进去,再没出来。后来每逢月圆,便有人听见里面诵经,可进去的人都疯了。”
“为什么叫哑窟?”阿元问。
老人摇头不语,只是用手指在喉咙处划了一道,随即抱起羊羔快步离去。
当夜,两人潜至窟前。洞口狭小,藤蔓缠绕,似已多年无人踏足。陈小满取出残灯,金芽微颤,叶片上的梵音竟与风声应和,形成一段断续低吟的偈语:
**“心非灯不照,魂非问不明。一念真名唤,万劫皆可倾。”**
他心头一震??这分明是《太初异录》中失传的“启灵咒”,唯有以真心叩问亡者姓名,方能唤醒其残识,破除执念。当年李忘忧曾言:“名者,魂之锚也。呼其名,则魂有所归;忘其名,则堕入虚妄。”
阿元点燃火把,率先钻入。洞内壁面布满壁画,色彩虽经千年风蚀仍隐隐泛光。第一幅画:七盏青铜灯悬于虚空,焰色各异,照彻幽冥。第二幅:七人持灯立于轮回门前,面容模糊,唯衣饰可辨身份??道士、僧侣、将军、农夫、妇人、童子、盲者。第三幅最为诡异:七灯合一,化作一轮金日坠入深渊,而深渊之中,竟伸出无数手臂,托举灯火,掌心刻字??**“我愿永眠,不愿醒”**。
“这不是渡亡图。”阿元声音发紧,“这是……献祭图。”
陈小满默然前行,心跳渐重。转过弯角,主窟豁然开朗。中央石台上,赫然供着一盏石灯,形制与他腰间残灯几乎一致。灯芯早已熄灭,但此刻却毫无征兆地自行燃起一道青焰!
火光映出对面整面墙壁的巨幅壁画:一名女子提灯伫立荒原,面前跪着一个孩童。她俯身轻语,唇形清晰可辨??正是“汝名谁”。
而那孩子抬头望她,脸上无悲无喜,双目空洞如井。
刹那间,残灯嗡鸣大作,金芽剧烈摇曳,竟自行脱落一片叶尖,飘向石灯。青焰触到金叶瞬间,轰然爆成金色火莲!整座洞窟骤亮如昼,壁画中人物似活了过来,光影流转,竟传出极细微的哭声、笑声、呼唤声……
“有人在这里封印过大量残魂。”陈小满闭目感应,“不止是死者的记忆,还有他们临终前最后一句未说完的话……全被抽离,凝在这壁画之中。”
阿元忽然踉跄后退:“你看那边!”
角落阴影里,盘坐着一具尸骨。身披破旧袈裟,右手结印,左手紧攥半卷经书。风沙未能侵蚀其骨,反倒在其头颅周围形成一圈奇异的气旋,细沙悬浮不落,如星辰环绕。
陈小满走近,轻轻取下经书。封面焦黑,仅余两字残痕:《**问名**》。
翻开第一页,墨迹如血:
>“吾乃西漠慈恩寺末代住持慧明,自知业障深重,特留此录,警醒后来者。
>归墟非外邪,实乃人心所聚之‘不愿别离’。昔年七玉结界崩塌,六门尽毁,第七门‘忆门’却因众生执念太深,反被逆炼为‘梦冢’,藏匿千万残魂于幻境之中。
>吾师曾得白鹿观秘传,习得‘问名渡魂术’,可唤醒迷魂,令其自愿赴死。然世人不愿放手,每每哀求:‘让他多留一夜’‘让她再说一句话’……久而久之,术者亦生贪念。
>我便是如此。
>我妻早逝,我以问名术召其魂归,初时仅见背影,后能对答,再后来……她开始做饭、缝衣、唤我法号。我以为是佛法无边,实则是我在不断填补她的空白。
>直到某日,她突然问我:‘慧明,我是谁?’
>我答不出。
>因为她早已不是她,而是我心中拼凑出的幻影。
>那一夜,我斩断执念,亲手焚去招魂幡。她最后一句话是:‘谢谢你,终于让我走了。’
>可此后十年,我仍在梦中见她。于是我明白??真正的归墟,不在地底,不在碑中,而在每一个不肯说再见的人心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