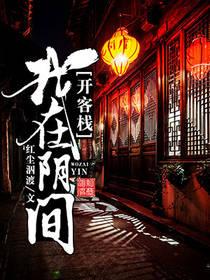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四合院之饮食男女 > 第118章 一年两次(第3页)
第118章 一年两次(第3页)
【今日雷阵雨,伴有强风;
?陈伯首次试戴助听器,将于岗亭露面(15:00-16:00);
?‘倾听志愿者’征集特别任务:为无法书写者代笔传信;
?请勿遮挡‘心灵信箱’投递口,已有十八封信等待回应。】
七颗星依旧相连。
午后风雨大作,电闪雷鸣。可到了三点五十五分,雨势渐弱,居民们撑伞聚集在岗亭外。孩子们踮脚张望,老人们裹紧外套,连平日避世的陈阿婆也被孙女搀扶而来。
四点整,门开了。
陈伯拄着拐杖走出,耳侧戴着一副银灰色助听器。他脸色苍白,手微微发抖,却挺直脊背,朝众人深深鞠了一躬。
苏晴站在身旁,准备翻译手语。
但他没打手语。
他张了嘴,喉咙滚动,发出一个沙哑、断裂、几乎不成调的音节:
“谢……谢……”
人群瞬间安静。
他又试了一次,声音稍稳:“谢??谢??你们……让我……听见……自己。”
泪水顺着他的皱纹滑落。三十年的沉默,碎在这两个词里。
苏晴哽咽着重复:“他说,谢谢你们,让他听见了自己。”
那一刻,伞下的每个人都湿了眼眶。不是因为雨,是因为一种久违的确认??原来被听见,真的能让人重新活过来。
接下来的日子,四合院悄然变化。
“倾听志愿者”名单不断延长,连小学生也组建了“童言无忌”小组,专门陪老人聊天、读报、画画。他们发现,许多老人其实不怕死,只怕遗忘。
“记忆之匣”升级为玻璃展柜,陈列着泛黄的信件、修复的录音带、林秀兰生前用过的搪瓷杯、陈伯建岗亭时的设计草图……每件物品旁都附有一段讲述文字。
最动人的是那口仿制井模型旁的新铭牌:
>**此处原为水井,1998年填埋。
>2023年重建为“静语池”,纪念林秀兰女士。
>愿所有欲言又止的声音,终得回响。**
某日清晨,王亚娟路过时,发现池边放着一只纸船,船上写着一行小字:
**“妈妈,我现在敢哭了。你听得到吗?”**
她没去查是谁写的,只是默默将它轻轻推入水中。
七月末,市里决定将四合院列为“城市情感遗产试点单位”,并拨款修缮公共空间。施工队进场那天,工头特意来找王亚娟:“领导说要拆掉岗亭扩建走廊,我觉得不合适,先问问你们意见。”
她摇头:“岗亭不能拆。”
“可它太旧了。”
“正因为旧,才值得留。”她说,“它是这座院子的耳朵。”
最终方案调整:岗亭保留原貌,周边加建半透明雨棚,既防风雨,又不遮视线。太阳能灯也升级为感应式,夜间自动亮起七彩光晕,象征七颗星的守望。
八月初,陈伯开始了每周一次的“无声对话课”。他在纸上写字,别人用手语或口语回应。第一次课上,他写下一句话:
**“我想告诉林秀兰,我每天都在替她看天气。”*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