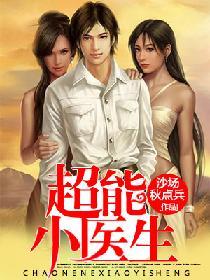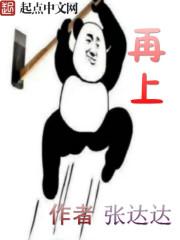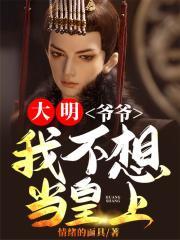笔趣阁>二婚嫁京圈大佬,渣前夫疯了 > 第1506章 他是棋子我是盟友(第2页)
第1506章 他是棋子我是盟友(第2页)
“你要把ECHO公开?”阿哲语气震惊。
“不是公开ECHO。”晨望着窗外初升的太阳,“是公开‘倾听’本身。我们要建一千间教室,每一间都配备最基础的录音设备和开放式声学设计,让学生们可以自由录制、播放、交换声音日记。不评分,不评比,不允许AI分析内容,只允许人与人之间互相听见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?”阿哲终于开口,“一旦这种模式扩散,传统心理干预体系、社交媒体算法推荐机制、甚至国家层面的情绪监控系统都会受到冲击。这不是项目,这是革命。”
“那就让它成为革命。”晨平静地说,“我们已经忍受太久‘被理解’的假象了。点赞不是回应,表情包不是共情,大数据画像更不是爱。现在,是时候让人类重新学习怎么当一个‘听者’了。”
三个月后,“回声教室”第一期试点在全国二十个城市同步落地。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李婉,在课堂上发起“无声周”挑战:全班学生不得使用任何电子通讯工具,只能通过面对面交谈或提交声音日记完成作业。
结果出人意料??原本沉默寡言的学生开始主动预约心理辅导室;一对长期冷战的母女在听完彼此的声音日记后抱头痛哭;更有学生自发组织“夜间听风社”,每晚十点在校门口架起麦克风,录制城市的声音,并配上自己的旁白解说。
一则视频在网络上悄然走红:画面中,一个戴着助听器的男孩第一次听到雷雨声,他捂住耳朵尖叫,却又忍不住笑出声来。“原来打雷不是机器坏了,”他说,“是天空在喊疼。”
与此同时,国际反响迅速升温。法国巴黎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引入“回声墙”概念,将教室外墙改造成可录音互动的声音装置,学生可以用手掌按压墙面留下语音留言。德国柏林一家养老院推出“遗言录音计划”,鼓励临终老人讲述一生中最想被人记住的故事,这些录音被制作成黑胶唱片赠予家属。
而在南美洲亚马逊雨林边缘的一个土著部落,传来了令人动容的消息:当地长老在接受“听风计划”培训后,开始用录音设备记录古老的口述神话。他们发现,当年轻一代戴上耳机聆听祖先的声音时,那些曾被认为“过时”的仪式与信仰,竟以全新的方式复苏。
世界正在缓慢地、笨拙地学会倾听。
然而,变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。
某夜,晨收到一条加密信息,来自国家安全局一位匿名官员:“‘认知安全组’内部出现分歧。部分高层认为‘回声教室’正在制造‘情感共振集群’,可能导致群体性意识波动,建议立即叫停并回收所有录音数据。”
他冷笑一声,回复道:“告诉他们,真正的危险从来不是人们听得太多,而是听得太少。若连倾诉都要被审查,那这个社会早已病入膏肓。”
话虽如此,他知道风暴迟早会来。
果然,半年后,《环球时报》内参版刊登一篇题为《警惕“情绪泛滥主义”侵蚀主流价值》的评论文章,直指“听风计划”及其衍生项目“助长个体主义情绪宣泄,削弱集体纪律意识”。紧接着,多个试点学校接到通知,要求暂停相关课程,接受意识形态评估。
舆论瞬间分裂。
支持者称这是“新时代的人文启蒙”,反对者则警告“放任私人情感传播将导致社会失序”。社交媒体上掀起激烈论战,有人上传视频,展示一名高中生在“回声教室”中崩溃大哭后被同学围坐安慰的画面,配文:“这才是教育该有的温度。”也有人放出截取片段,强调“学生整日沉浸在负面情绪中,无法专注学业”。
压力如潮水般涌来。
就在外界猜测项目即将终结之时,小满站了出来。
她在一场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论坛上发表演讲,全程未提数据、政策或理论,只讲了一个故事:
“我五岁那年,爸爸带我去医院做语言评估。医生问我:‘你能模仿我说话吗?’我说不出话,只能摇头。他又问:‘那你能写字吗?’我也不能。最后他说:‘这孩子可能永远都不会说话了。’
我看见爸爸的手攥得很紧,但他一句话都没说。回家的路上,他买了台老式录音机,开始每天录下我的呼吸声、脚步声、翻书声……他对我说:‘没关系,你说什么我都听得见。’
后来我才明白,他不是在等我说话,而是在告诉我:你的存在本身就有声音。
所以今天我想问所有人:当我们害怕别人的情绪,是不是因为我们从未被真正听过?当我们急于评判别人的脆弱,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敢承认自己也需要帮助?”
台下寂静无声,继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三天后,教育部发布公告:“回声教室”项目调整为“校园心灵空间建设示范工程”,纳入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升级计划,资金与政策支持全面落地。
风波暂息。
但晨知道,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
一年后的春天,他再次踏上云南的土地。这一次,他是去参加“听风计划”十周年纪念仪式。老屋已被改建为一座小型纪念馆,外墙刻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留言:
>“谢谢你让我知道,哭也可以是一种勇敢。”
>“我在这里留下了对亡妻的最后一句话。”
>“我终于敢说:我很孤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