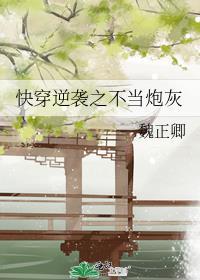笔趣阁>都重生了谁考公务员啊 > 第687章陈培松和毛晓琴的棒打鸳鸯(第2页)
第687章陈培松和毛晓琴的棒打鸳鸯(第2页)
走出会议室时,阳光刺眼。林小雨问他:“值吗?为了这点进度,耗了这么多精力。”
“值得。”他说,“你知道为什么飞机起飞最费油吗?因为要克服地面摩擦力。一旦离地,反而轻松了。”
夏天来临之际,南方暴雨成灾。湖南岳阳一处堤坝出现管涌,常规监测设备因洪水失效。紧急关头,当地水利局联系“重启人生”湖南分部,请求支援一支由渔民组成的“民间智测队”。这些人曾接受过简易水文传感器组装培训,能在半小时内搭建临时监测网络。他们在齐腰深的水中作业,用塑料桶浮载设备,通过蓝牙将数据传回指挥中心。正是这套土法上马的系统,提前预警了二次溃口风险,为疏散争取了宝贵时间。
事后,应急管理部专门致函感谢,并提议将此类“群众性技术自救组织”纳入地方应急预案备案体系。
陈着看到新闻时正在高铁上。窗外稻田连片,绿意盎然。他打开笔记本,写下一段话:“教育的本质,不应是筛选适配现有社会结构的人,而是培养能够改造社会结构的人。当灾难来临时,拯救我们的或许不是一个名校博士,而是那个曾经被认为‘读不进书’的渔夫,因为他知道水流的脾气,也学会了倾听机器的语言。”
七月流火,项目迎来新一轮扩张。六省联动启动“乡村CTO计划”,选拔五十名优秀学员赴浙江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交叉学科集训,课程涵盖农业工程、人机交互与社区治理。结业后,他们将作为“村级技术协调官”派驻基层,协助村委会制定数字化转型路径。
扎西成为首位藏族学员。临行前,村里人为他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送别仪式:老人们往他行李里塞糌粑和经幡,孩子们用彩笔画了一架“会飞的牦牛”送他。“你要替我们看看杭州有多大。”次仁阿妈拉着他的手说。
培训期间,扎西提出一个构想:开发一款基于藏语语音识别的智能巡护系统,能让年迈的守山人对着手机说出发现的问题,自动生成上报文本并定位坐标。浙大教授惊叹于其需求洞察力,当场决定将其列为校地合作重点项目。
与此同时,龙小雨在非洲完成了首轮授课。她在乌干达一所女子中学建立了第一个海外“少年创客角”,用废旧手机和太阳能板拼凑出简易机器人。有个女孩用它帮母亲搬运柴火,笑着说:“我现在是妈妈的机械臂。”视频传回国内,无数网友留言:“原来改变世界,真的可以从小事开始。”
秋季到来时,一场突如其来的政策调整打乱节奏。某省份宣布暂停采购第三方培训机构服务,要求各地职教资源统一归口管理。此举直接影响八个正在进行中的县域项目,数百名待就业青年面临课程中断。
王磊再次提议收缩战线:“地方政府态度变了,我们得现实点。”
陈着却摇头:“这不是退让的时候。他们想要整合,那就让我们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。”
他亲自带队奔赴该省会城市,连续三天拜访教育、人社、财政三部门,提交详尽运营报告与社会效益分析。最终促成一项创新合作模式:由政府提供场地与基础师资,溯回科技输出课程体系与技术支持,共同成立混合所有制办学实体。既满足监管要求,又保留灵活性。
“我们不是来抢饭碗的,”他在谈判桌上说,“是来添筷子的。多一个人吃饭,不代表饭就少了,反而可能催生更大的餐桌。”
冬雪初降时,新模式已在三个地市落地见效。更令人振奋的是,首批参与项目的学员中有七人通过竞争上岗,成为县级技能培训中心主任助理,实现了从受助者到管理者身份的转变。
除夕夜,陈着再次组织跨年直播。这一次,连线点增至十五个,包括南极科考站的一名后勤technician??他曾是东莞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人,通过自学考取极地运维资格证。镜头里,他站在冰原上挥手:“这里的风比老家还冷,但我觉得特别踏实。因为我终于成了别人需要的人。”
零点钟声响起,千万观众见证了一句新口号诞生:“我不怕起点低,只怕不动手。”
新的一年,春天的消息接踵而至。国家发改委印发《关于推动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》,明确提出“构建人人皆可成才、人人尽展其才的终身学习生态”。文中多次引用“重启人生”案例,称其“探索了技术普惠的新范式”。
四月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邀请陈着出席全球教育峰会。当他站在巴黎会场讲述阿里之夜的篝火与银河时,台下许多发达国家代表沉默良久。一位北欧教育部长感慨:“我们总以为创新来自实验室,可你们证明了,它也可能诞生于一片冻土上的帐篷课堂。”
回国后,他收到一封信,寄自甘肃一个偏远山村小学。信纸泛黄,字迹歪斜,是一位五年级女生写的:
“陈老师你好,我是看了龙姐姐的节目才敢给你写信的。我也想学电脑,但我们学校只有两台坏掉的旧机子。校长说没钱修。你能教我拼音吗?我想先学会打字,然后告诉全世界,我们村的杏花开了。”
他盯着信看了很久,然后转发给技术团队:“做个离线版识字APP吧,适配最低配置的安卓机,名字就叫‘杏花开了’。”
几天后,这个轻量级应用上线,无需联网即可运行,内置方言语音对照功能。首周下载量突破二十万,覆盖三千多个行政村。
某夜加班结束,他独自走在空荡的走廊。路过一面镜子时停下脚步,忽然笑了。镜中人依旧穿着洗旧的衬衫,袖口磨了边,头发乱糟糟的,可眼神依旧像二十年前那个坚信“知识能改命”的少年。
他知道,这条路没有终点。质疑还会再来,偏见不会一夜消失,体制的齿轮转动缓慢而沉重。但他也看见,在无数个他曾踏足或未曾抵达的地方,有人正拿着他编写的教材、用着他设计的工具、沿着他铺下的轨道,一步步走出属于自己的重生。
这个世界依旧坚硬,
但裂缝之中,光已成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