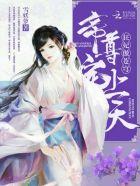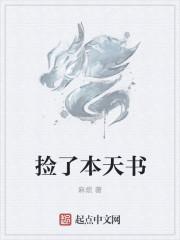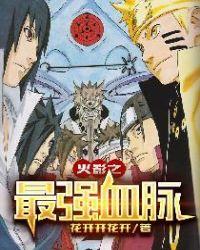笔趣阁>魅力点满,继承游戏资产 > 第七百一十四章 忍了认了从了日常(第3页)
第七百一十四章 忍了认了从了日常(第3页)
团队紧急排查,最终发现这源于一所山区小学的心理辅导课。老师让学生们写下最想对逝去亲人说的话,统一上传至“回声计划”公共信箱。其中一个孩子写道:“我把信读给同桌听,他说他妈妈也一定能听见。我们就约好每天写一封,让妈妈们在天上也能交朋友。”
于是全班三十个孩子,每人每天坚持写信,有的画图,有的录音,有的请老师帮忙打字。他们相信,只要不停地说话,那边的人就不会寂寞。
消息传开后,全国上百所学校自发组织“写给天堂的一封信”主题活动。有幼儿园小朋友用蜡笔涂满整张纸:“爸爸,我画了恐龙,你最喜欢那只霸王龙!”也有高中生认真写下:“外婆,我考上医学院了,以后我要治好所有像你一样的病。”
沈玉言看着后台不断涌入的稚嫩笔迹,泪流满面。
她下令特别开通“童年回声”专属通道,为未成年人提供定制化交互界面,并联合教育部门编写《儿童哀伤辅导指南》。同时,她亲自撰写一封公开信:
>“亲爱的孩子们:
>每一封信,我们都收到了。
>那些笑声、涂鸦、歪歪扭扭的字,全都安全抵达。
>你们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,一定都看到了。
>因为爱,是最强的信号。
>它穿越生死,永不消码。”
这封信用彩色字体发布在官网首页,配图是一群孩子仰头放风筝的照片。
几个月后,首座“回声图书馆”实体馆在杭州奠基。选址就在西湖边一片废弃的老邮局遗址,象征“未送达的信终将找到归途”。建筑外观设计成翻开的书页形状,内部设有沉浸式记忆厅、黑胶唱片刻录坊、静思庭院与志愿者培训中心。
奠基仪式上,沈玉言站在人群中,没有致辞,只是将那本唐仪的日志复印件放入时间胶囊,埋入地基之下。
旁边的小周低声问:“你说,将来会不会有人读到这本书,然后也变成下一个‘我们’?”
她望着远处湖面粼粼波光,轻轻说:“一定会的。”
那天傍晚,她再次梦见那个无限延伸的图书馆。
唐仪依旧穿着白大褂,站在柜台后整理书籍。见到她,笑着递来一本封面空白的册子。
“轮到你写新故事了。”她说,“这次,不用再等谁醒来。”
她接过书,翻开第一页,提笔写下标题:
《如何教会人类好好说再见》
醒来时,晨光洒满房间。她起身拉开窗帘,看见楼下街道上,一个穿校服的女孩正把一封信塞进“回声驿站”的投递口。风吹起她的马尾,也吹动手中那张纸的一角,仿佛一只振翅欲飞的蝶。
她拿起手机,打开应用后台,默默将昨日新增信件数截图保存。
23,108。
每一个数字背后,都是一个不肯放弃爱的人。
她戴上那条米白色围巾,走出家门,朝着驿站走去。
阳光很好,照得玻璃幕墙通体透明,墙上的粉笔字在光中闪闪发亮:
“我想你了。”
“你还好吗?”
“今天,我活得还不错。”
风穿过树林,带着春末特有的温润气息。
而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,也许正有人微笑着读完这些话,合上书页,轻声回应:
“我知道了。我一直都在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