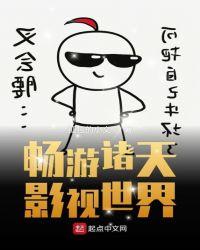笔趣阁>从机械猎人开始 > 第九十九章 交易申请(第2页)
第九十九章 交易申请(第2页)
她蹲下身,手指抚过其中一根铁轨的接缝处。
然后,她开始轻敲。
指甲、指节、掌缘,轮流敲击不同的位置,节奏缓慢却不迟疑,像是在读一首盲文诗。每一下敲击之后,铁轨都会传出不同音高的共鸣,有些清越如铃,有些沉闷如鼓。很快,整条废弃铁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乐器,声音顺着金属蔓延数十公里,惊起沿途栖息的飞鸟。
但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是??
**铁轨在回应她。**
不是简单的物理共振,而是有意识的应答。某些区段会在她停顿时自行震动,发出特定频率的颤音;有些断裂处的锈渣会在特定节奏下簌簌脱落,露出底下完好如新的合金内层;甚至有一段完全埋在土里的旧轨,在她敲击对面轨道后,竟缓缓抬升,破土而出,像蛇一样蜿蜒扭动,最终摆成一个完美的圆形。
科学家后来称此现象为“记忆金属觉醒”,认为这些钢材中含有某种未知纳米涂层,能够记录并重现已逝去的人类活动轨迹。但阿喃知道,这不是技术问题。
这是**思念的形状**。
这条铁路曾运送过千万旅人,承载过无数离别与重逢、欢笑与哭泣。那些情感并未随时间消散,而是以振动的形式烙印在材料深处,等待一个愿意倾听的人来唤醒。
她继续敲击。
第四天清晨,整条铁路完成了自我重构。所有断裂处自动焊接,扭曲部分校准归位,腐烂枕木被地下生长的坚韧藤蔓替代,形成天然缓冲结构。当第一缕阳光照在轨道上时,一辆从未登记过的蒸汽机车缓缓驶来。
它没有司机。
车身漆黑,烟囱冒着淡淡的白雾,车轮转动时发出的不是金属摩擦声,而是一首老式广播里常放的民谣口琴曲。列车停在阿喃面前,车门无声开启,车厢空无一人,唯有一张木椅摆在中央,上面放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。
她认得那本子。
是林远年轻时随身携带的采风记录册,曾在一场火灾中遗失。她曾以为它早已化为灰烬。
她走进车厢,翻开第一页。
纸上空白。
可当她将耳朵贴近纸面,却听见了千万人的声音??那些曾在铁路上奔波过的乘客,他们的对话、歌声、咳嗽、叹息,全都压缩在这几页纸中,如同被封印的魂灵。再往后翻,字迹逐渐浮现,全是她熟悉的笔迹,却是她从未写过的内容:
>“当你看到这些字时,我已经不在你身边。
>但我从未离开。
>我活在每一次风吹过电线的嗡鸣里,
>活在孩子踩水坑时溅起的噼啪声中,
>活在老人摇扇子的节奏里,
>活在你吹笛子前那一声轻轻的吐气里。
>听见了吗?
>那就是我在说:我在这里。”
阿喃合上本子,泪水滴落在封皮上。
列车缓缓启动,沿着新生的轨道驶向远方。没有人知道它要去哪里,也没有人试图阻拦。沿途城镇的居民只是默默站在窗前或门口,听着那悠扬的口琴旋律渐行渐远,心中莫名涌起一股久违的安宁。
而阿喃,再也没有下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