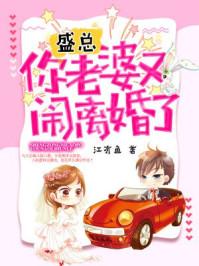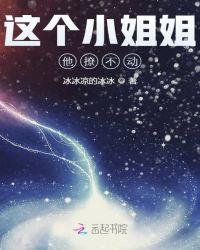笔趣阁>毒妃她从地狱来 > 第1172章 真是阴魂不散(第3页)
第1172章 真是阴魂不散(第3页)
紧接着,更多影像浮现:
盲眼老妪在沙漠中摇铃;
牧羊少年阿岩在石碑前献花;
小满在竹屋教孩童写字;
林小禾走进博物馆,肩头落下一朵紫花……
最后,所有画面融合成一句话,由亿万人的声音叠加而成,响彻天地:
>**“我们记得你。”**
刹那间,忆心珠爆裂开来,化作万千光点,如萤火升腾,飞向四面八方。
与此同时,全国各地的共忆分馆同时震动。
长安的铜镜映出裴宛的身影,对她母亲遗留的绣帕微笑点头;
江南的祠堂牌位自动排列成“裴”字形状;
西北戈壁的沙地上,一夜之间长出整片铃形花海,随风发出清越铃音。
最惊人的是,太傅府旧址的地窖深处,尘封已久的陶罐自动破土而出。罐中赫然是三百二十七张写满名字的纸条,纸面完好如新,墨迹未褪。经辨认,其中竟有数十人是当今朝中大臣的先祖??他们并非死于战乱或疫病,而是因私自记录民间苦难,被朝廷秘密处决。
冤忆司立即介入调查。短短三日,七名高官主动请辞,两名皇亲国戚被软禁。新帝下令:凡涉及毁忆篡史者,无论亲疏,一律革职查办,子孙三代不得入仕。
而裴砚,在收到陶罐与碑文残片后,整整三天未出房门。
第四日清晨,他亲手将裴宛的遗书、断簪、玉雕、信件,连同那张写着“芜归”的黄纸,一同放入新制的檀木匣中。然后,他提笔写下最后一部《民忆录》补遗,共十三卷,题为《亡者之名》。
他在序言中写道:
>吾妹一生,未尝识一字,未写一名。
>然天下女子,自此可名可书,可言可忆。
>此即她以命换来的光。
>我不敢称功,唯愿后人读此书时,
>能想起那个十二岁的女孩,
>在黑暗中,仍想着??
>**要认字,要留名。**
书成当日,裴砚焚香沐浴,穿戴整齐,端坐于案前,闭目而逝。
共忆馆为其举行国葬,百姓自发沿街跪送。灵车经过之处,万人手持铜铃,齐声诵念:“裴宛,我们记得你;裴砚,我们记得你。”
当灵柩抵达千灯书院后山,安葬于小满与柳知言之间时,天空忽降紫雨。雨滴落地不湿,反而化作一朵朵铃形花,在三人墓前连成一片花海。
林小禾跪在墓前,将《亡者之名》放入墓穴。
她轻声说:“先生,阿芜,小满老师,你们走过的路,我们继续走。你们点亮的灯,我们继续燃。”
夜深人静时,她独自留在山上。月光洒落,忽然听见一阵极轻的铃声。
她回头,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花海尽头??是少女模样,手持铜铃,穿着旧时布衣,眉眼温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