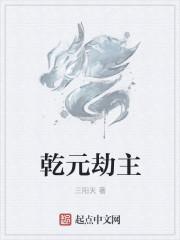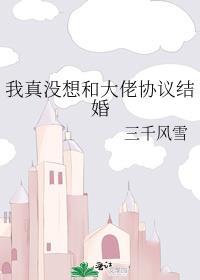笔趣阁>逍遥四公子 > 第1945章 冯奇正 看到没这就是典型的无病呻吟(第2页)
第1945章 冯奇正 看到没这就是典型的无病呻吟(第2页)
沈知白将此事录入笔记,并特意标注:“张砚生非医者,然因曾读《守望录》中‘救人一命,胜造七级浮屠’之语,遂自学医理三年,随身携药以备不时。”
张砚生摇头:“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”
“这正是最难得的。”沈知白望着他,“你没有等别人来救,也没有抱怨制度缺失。你选择了行动。”
一路前行,类似之事屡见不鲜。他们在河边救起一名欲投水的老渔夫,原是他独子战死边关,家中无依;沈知白代笔写信至兵部,请查抚恤遗漏名单;半月后,公文抵达,老渔夫终得半亩薄田安度晚年。他们在小镇集市遇见一群流浪少年,靠乞讨维生,却自发组织起来照顾更小的孩子。张砚生提议设立“少年互助班”,教他们识字算账,学习谋生技能。一个月后,这些孩子开始帮商户记账、送信,甚至合伙开了个小杂货铺。
每当有人问起缘由,他们总说:“有人教我们要做个有用的人。”
这一日,他们抵达南陲边镇“落桐”。此地偏僻,山路崎岖,百姓多以采药为生。镇口立着一块石碑,上书:“宁可空山十载无人,不可一日无义。”沈知白读罢,肃然起敬。进镇后才知,此地曾遭大疫,全镇几乎灭绝,唯有一名老药师冒死研制解毒汤,救活数十人。他自己却因试药中毒身亡。临终前,他将配方刻于石壁,并留下一句话:
>“药可救人一时,心善方可济世万代。”
当地人建祠供奉,称其为“义翁”。每年清明,全镇百姓齐聚祠前,诵读《守望录》中关于仁医的篇章。而最令人动容的是,自那以后,落桐镇凡习医者,必先立誓:“不收穷苦人诊金,不死前不停施药。”
沈知白泪流满面,当场决定将此地列为“守望学堂”第十州试点。他连夜起草章程,提出“以义养学,以学传义”的理念:学生免费入学,但毕业后须返乡服务三年,或资助一名寒门学子完成学业。
消息传出,四方响应。短短两月,便有十七位年轻医师自愿前来执教。其中一人,竟是当年被救孩童的孙子。他带来祖父亲笔整理的医案集,扉页写着:“祖父说,他的命是别人换来的,所以他这一生,只能用来还债。”
沈知白将这一切编入《守望录?续编》第一章,并在卷首题辞:
>**所谓善,不过是把别人给你的光,再照向另一个人的眼睛。**
此时,距林隐最后一次现身已逾十五年。世间关于他的传说渐少,取而代之的是无数平凡人的壮举。北方战场退役老兵组建“护童队”,专程接送偏远村落儿童上学;东南沿海渔民自发成立“救难舟团”,每逢风暴必出海搜救遇难船只;西部商旅联盟设立“义仓”,沿途免费提供饮水干粮。每一桩善行背后,几乎都能找到一句出自《守望录》的话,或一段口耳相传的故事。
而那九十九座驿站,也早已超越传递文书的功能,成为流动的精神据点。每站皆设“心声墙”,供过往行人留言倾诉;墙上贴满纸条,有感恩、有忏悔、有承诺、有寻人启事,更有无数稚嫩笔迹写着:“我也想做一个好人。”
某夜,沈知白独坐驿站灯下整理稿件,忽觉胸口发热。他解开衣襟,只见贴身佩戴的玉佩竟泛出淡淡青光??那是记事人传承信物,唯有感应到重大“心光”波动时才会显现。他猛地站起,奔出屋外,仰望苍穹。只见南方天际,一颗星辰骤然明亮,划破夜幕,宛如流星坠地。
他当即召集驿站众人,备马启程。七日后,抵至一处深谷。谷中雾气缭绕,溪水潺潺,竟生长着一片罕见的蓝花铃草??传说中只有在至善之地才能绽放的植物。草丛中央,有一座简陋茅屋,门扉半开,屋内无人,唯有一张木桌、一盏油灯、一本摊开的册子。
沈知白走近细看,顿时跪倒在地。
那是全新的《守望录》手稿,纸张泛黄,墨迹犹润。首页写着:
>**《最后的章节》**
>
>我已走不动了。
>这双脚踏过雪山、荒漠、战场、疫区,见证过太多泪水与希望。
>如今,它们只想安静地歇在这片开满蓝花铃草的山谷里。
>
>但我仍要写完这一章。
>因为我知道,总会有人来取走它。
>就像当年我接过阿砚的遗稿一样。
>
>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苦难,而是冷漠。
>当一个人看见别人的痛苦却转过头去,黑暗就开始蔓延。
>可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停下脚步,问一句“我能做什么”,光明就不会断绝。
>
>所以,请继续写下去。
>不是为了纪念我,而是为了提醒后来者:
>善良不需要伟大,只需要坚持。
>教一个孩子写字,扶起一个跌倒的老人,倾听一次无声的哭泣……
>这些微小的选择,终将汇成改变时代的洪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