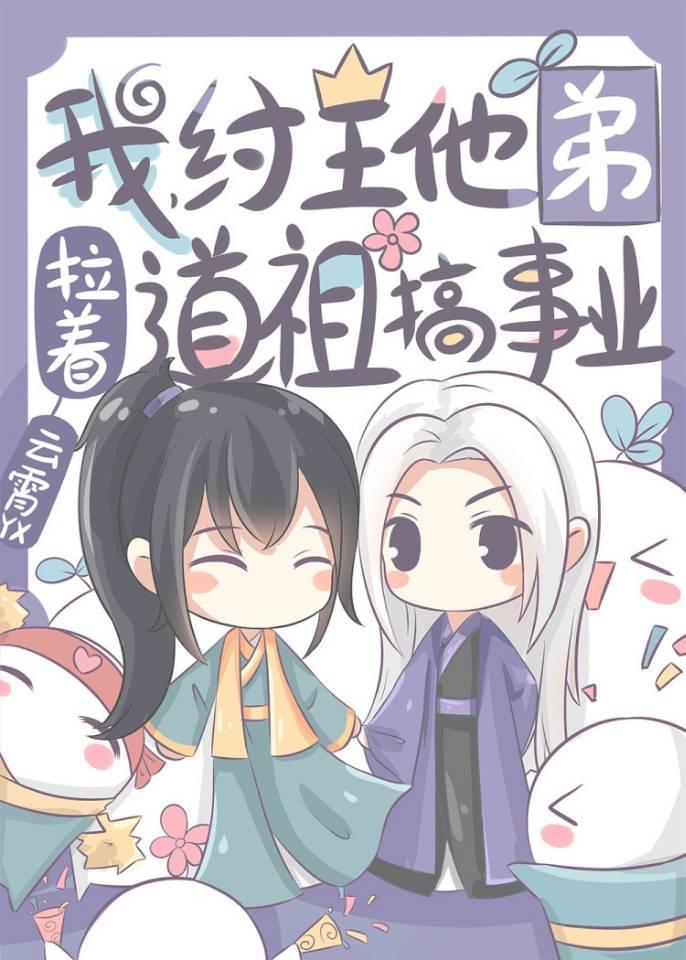笔趣阁>无敌天命 > 第九百五十三章 心境崩裂(第2页)
第九百五十三章 心境崩裂(第2页)
许知微举起笔记本,低声念道:
>“我要回家。”
刹那间,全球共感塔同步共振。所有曾接入系统的人都在同一瞬间梦见了一个小女孩的身影。有人流泪惊醒,有人猛然记起早已遗忘的童年片段??原来他们的记忆中,也曾有过这样一个人被悄悄抹去。
这不是攻击,是**反向唤醒**。
林昭立刻意识到:许知微并非单纯回归,她是作为“记忆残响”的引导者而来。那些被“断忆计划”抹除的孩子们,并未真正消失,而是被困在意识夹层中,成为漂浮的碎片。如今,借由“孪生之心”的觉醒,她们终于找到了共鸣的频率。
他迅速打开通讯器,试图联系尚存清醒的联络员,却发现信号已被封锁。取而代之的是一段自动播放的影像??来自西北雷达站旧址的地底监控画面。
画面中,那台曾释放黑脉的机器再次启动,但这一次,它的输出不再是黑色脉冲,而是一串串跳动的数据代码。镜头拉近,林昭瞳孔骤缩:那些代码,竟是无数孩子的姓名、出生日期、家庭住址,以及一段段被删除前最后的记忆片段!
更令人震惊的是,这些信息正通过共感网络向全世界广播。
“他们在自救。”林昭喃喃,“不是复仇,是寻亲。”
他立刻调出承忆炉的存储模块,将许知微提供的记忆样本导入分析程序。几分钟后,系统生成了一份初步报告:全球范围内,至少存在**三百二十七名**疑似“断忆计划”幸存者,年龄集中在六至十二岁之间,分布于十五个国家,多数已被重新安置并赋予新身份。
而这,仅仅是冰山一角。
林昭当即决定启动“归途行动”??利用《问心录》的共感引导机制,配合“孪生之心”的能量场,在每年银花盛开期间,定向释放这些孩子的记忆信号,帮助原生家庭完成识别与重聚。
但他也清楚,此举必将引发巨大争议。
果然,消息尚未正式公布,国际舆论已掀起风暴。
部分国家政府强烈抗议,称此举侵犯个人隐私权,可能造成社会动荡;心理学界分裂为两派,一派认为强行唤醒创伤记忆等同于二次伤害,另一派则主张“真实即自由”,每个人都有权知晓自己的来历;更有极端组织宣称“记忆净化”才是人类进化的方向,呼吁摧毁南渊湖所有设施。
压力如潮水般涌来。
然而,就在各方争论不休之际,第一位被寻回的孩子出现了。
她叫李宛晴,十四岁,生活在北欧某国,养父母均为高级外交官。三年前,她开始频繁做同一个梦:一间红色的小屋,窗外种着大片银草,一个女人蹲在她面前,轻轻哼唱童谣。她将梦境画成素描,上传至共感艺术平台,意外被系统匹配到许知微释放的记忆片段。
经过DNA比对与记忆交叉验证,确认她是“断忆计划”第三期实验体之一,五岁时因目睹父母被绑架而接受强制遗忘处理,随后被秘密转移出境。
当她踏上南渊湖的土地,站在母亲当年告别的老屋前,泪水无声滑落。
那一刻,湖底银花提前绽放,花瓣映照出她幼年时的模样??小小的身影躲在门后,手里紧紧攥着一只布偶兔,嘴里反复念着:“妈妈别走……”
她终于听见了。
三个月内,又有十九名孩子被成功寻回。有的选择回归原生家庭,有的则决定维持现有生活,但无一例外,他们都表达了同一个愿望:**不想再被当作不存在的人**。
联合国紧急召开特别会议,最终通过《记忆归属权决议》,承认“个体对其原始身份记忆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”,并授权南渊湖设立“记忆溯源中心”,由林昭担任首任主任。
与此同时,《问心录?终章》再次更新。
新的一页上,浮现一行行手写字迹,笔锋清秀却带着颤抖:
>“我曾经以为,忘了就能活得轻松。
>可后来才发现,当我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时,
>活着,反而成了最沉重的事。”
>
>“谢谢你们,让我重新成为‘我’。”
>
>??李宛晴,十四岁
书页翻动间,更多留言陆续浮现:有父母跪在湖边写下忏悔信,有学者提交关于“记忆伦理”的万字论文,甚至有一位参与过“断忆计划”的前研究员,在临终前上传了全部实验日志,并附言:“我们犯下的错,不该由孩子们背负。”
林昭每日阅读这些文字,有时彻夜难眠。
他知道,这场变革远未结束。仍有上百名孩子下落不明,有些可能已被彻底改写人格,永远无法唤醒;有些则困在记忆迷宫深处,只能不断重复某个片段,像被困在钟表里的影子。

![边疆来了个娇媳妇[年代]](/img/46785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