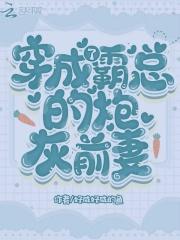笔趣阁>无敌天命 > 第九百六十章 你是个什么东西(第2页)
第九百六十章 你是个什么东西(第2页)
>“我们一直在等一个愿意接纳我们的宿主。”少年低声说,“不是消灭我们,也不是囚禁我们,而是……拥抱我们。”
林昭猛然惊醒,冷汗浸透后背。终端数据显示,他的脑电波曾一度与陈默完全同步,持续达十四分钟,创下历史纪录。
“你看到了什么?”老周焦急地问。
林昭喘息着,一字一句道:“我们错了。一直以来,我们都以为‘唤醒’就是终点。可真正的救赎,不是让人从沉睡中醒来,而是让那些被放逐的记忆,重新回家。”
第二天清晨,五座“记忆对话中心”同时发布公告:启动“归忆计划”??邀请全球所有接受过记忆干预的人,自愿参与“影忆体重构实验”。目标不是治愈,而是整合;不是消除痛苦,而是赋予其意义。
响应者远超预期。
三个月内,超过两万名曾接受过不同程度记忆调控的个体报名。有些人甚至来自尚未公开承认“日蚀”存在的国家,通过地下网络辗转抵达南渊湖。
小满成了这场实验的核心引导者。她虽仍无法流畅言语,但她创造了一套全新的视觉符号系统,能精准映射不同类型的记忆创伤。每当有人进入冥想状态,她的画笔就会自动在特制画布上勾勒出对方内心世界的轮廓,帮助技术人员判断“影忆体”的位置与情绪强度。
第一例成功融合发生在第四十九天。
一位名叫苏婉的女性,在童年目睹父母死于空袭后,被强制清除了相关记忆。成年后她成为和平大使,却始终无法建立亲密关系。接入系统后,她的“影忆体”显现为一个八岁的小女孩,躲在衣柜里瑟瑟发抖,手中紧攥着半张全家福。
经过七轮共感对话,苏婉终于对着那个小女孩伸出手:“我听见你了。我不再怕你了。你是我的一部分,也是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。”
当她们相拥的瞬间,整个南渊湖基地的能量读数骤然飙升,银草齐齐绽放,花瓣散发出微弱蓝光,如同星辰落地。
然而,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一变革。
某夜,基地外围监控捕捉到一组神秘信号,伪装成气象数据包,实则携带一段加密指令,试图远程劫持主服务器中的《创世纪录》备份文件。攻击来源无法追踪,但老周在解码过程中发现了熟悉的语法结构??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“心智盾牌”项目的专属编码方式,早已随冷战结束而失传。
“有人不想让我们揭开真相。”李宛晴凝视着代码片段,“而且,他们还在用老方法做事。”
紧接着,安第斯山脉的分部传来噩耗:一名刚完成记忆融合的志愿者在返程途中遭遇车祸,车辆失控冲下悬崖。奇怪的是,黑匣子记录显示,司机在最后一刻突然大喊:“我不是我!”随后主动松开了方向盘。
阿川带队赶赴现场调查,发现车内残留微量神经抑制剂成分??正是“日蚀”初期使用的那种能让意识短暂离体的药物。
“这不是意外。”他咬牙道,“是清除。有人在猎杀那些‘完整’起来的人。”
林昭知道,阴影从未离去。它只是换了面具,藏得更深。
于是他做出决定:重启“追忆日”,但这一次,不再只是纪念,而是宣战。
他在全球直播中宣布:“从今往后,每年这一天,我们将公开一段被掩盖的记忆。不论来自个人、组织还是国家,只要证据确凿,我们就让它重见天日。你们可以封锁信息,可以抹杀证人,但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记住,我们就不会停下。”
反响如潮。
第一年,“追忆日”公布了三十七段尘封录像:某国高层在会议室笑着讨论如何制造饥荒以控制人口;一群医生在实验室给儿童注射未经测试的记忆阻断剂;一位记者临终前录下的口述,揭露自己如何被迫诬陷无辜者……
每一段播出,都有成千上万人跪在镜墙前痛哭。
而银草,每年都在那一夜开出最盛大的花海,仿佛大地也在替人类忏悔。
小满画了一幅新的作品:一棵巨树扎根于地球核心,根系由无数交织的记忆丝线构成,枝干伸展至星空,每一片叶子都是一个人的脸。她在下方写道:**我们不是要忘记疼痛,而是要学会带着它生长。**
林昭将这幅画挂在“记忆圣殿”的中央大厅。
某日深夜,他再次梦见妹妹。这次她已长大,穿着校服,背着书包站在家门口等他放学。她回头一笑:“哥哥,今天老师讲了关于勇气的故事。我说,我哥哥就是最勇敢的人。”
他醒来时,窗外月光洒在床头那本《记得的权利》上,书页恰好翻到最后一章。
他轻轻合上书,走到窗前。远处,“念”正坐在湖边石凳上,翻开那本黑色笔记本,一笔一划写着什么。林昭没有打扰他。他知道,有些话不必说出,也能被听见。
风起,银草轻摇,沙沙作响。
像无数人在低语。
像整个世界终于学会了倾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