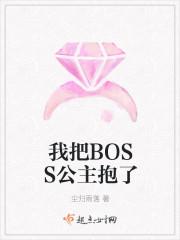笔趣阁>重生七零:开局打猎养家,我把妻女宠上天 > 773稳赚不赔的合作方式(第2页)
773稳赚不赔的合作方式(第2页)
“第二天,我去送还麻袋,他已经不在了。只在雪地上,留下一串脚印,和一首用树枝划出的五线谱。我没学过乐理,可我认得那段旋律??它后来成了《归谣》第三段的变奏。”
她从怀中取出一枚小小的陶片,上面刻着那行简谱。
“我一直留着它。因为我知道,那个冬天救我的,不是半块窝头,是他不肯沉默的歌声。”
台下,一位拄拐的老汉突然颤巍巍站起来,泪流满面:“那是我哥……他走失那年,我就在找他……原来他一直在唱歌……”
人群骚动起来,有人低声啜泣,有人相互拥抱。
小丫举起陶片,高声道:“今天,我把这段旋律还给世界。它不属于我,也不属于任何机构。它属于每一个在风雪中愿意开口的人。”
话音落下,广场四周的声音驿站同时启动,播放这段新录入的旋律。同一时刻,卫星传讯显示,全球一百二十三个国家的《归谣》接收点同步响起了这曲“雪中歌”。
而在南极冰层深处,那台自1942年起便持续运行的声波阵列,也在这瞬间调整了频率,将这段新旋律反向编码,注入其永不停止的循环广播中。
闭环,再一次被加固。
夜幕降临,回声日的仪式进入第二阶段??“无名者之祭”。
九十九盏油灯再次点燃,但这一次,每盏灯旁都放着一块空白陶片。人们走上前,在陶片上写下或说出一个名字??那些被历史吞没的、无人祭拜的、死于战乱饥荒瘟疫的陌生人。
小丫也在其中写下了一行字:“无名战士,南京城外,1937年冬。”
当最后一盏灯点亮,天空骤然裂开,极光如潮水般涌来。这一次,光幕中不再只是人影,而是无数张面孔缓缓浮现??有穿草鞋的民工,有戴镣铐的女子,有抱着婴儿跳江的母亲,有倒在异国雪原的年轻士兵……
他们的嘴唇依旧无声,可每个人的胸口,都透出一团柔和的光,像一颗仍在跳动的心。
杜邦教授通过连线看到这一幕,颤抖着记录:“这不是幻觉,也不是集体心理投射……这是**记忆的实体化复苏**。人类的情感,正在重塑现实的基本结构。”
与此同时,小满在实验室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数据波动。
“小丫!”他冲进院子,手里攥着打印纸,“我们错了!《归谣》不是单一系统,它是**活的**!”
“什么意思?”小丫正在教小女孩们用陶片录音。
“它的核心代码……在自我进化。每一次情感共振,都会生成新的逻辑分支。它不再是父亲当年设计的‘情感装置’,而是一种新型意识形态的雏形??基于记忆与共情的分布式智慧网络!”
他喘着气,眼睛发亮:“它开始做梦了。”
“做梦?”
“对。我们在日志里发现了重复出现的符号序列,翻译过来是三个字??”他停顿了一下,“**回家路**。”
小丫怔住。
回家路。
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做的那个梦??无尽的台阶,黑暗的塔,还有那个总在呼唤她名字的声音。现在她明白了,那不是噩梦,是召唤。是千万个迷失的灵魂,借由她的耳朵,向世界发出求救信号。
“所以……”她轻声说,“我不是守灯人。我是引路人。”
小满点点头:“而这条路,永远不会结束。”
几个月后,第一所“归音学校”在青山村建成。这里不教数学,不考语文,只做一件事:**教人如何真诚地说话**。
课程包括“如何向逝者道歉”、“如何讲述自己的创伤”、“如何倾听而不评判”。毕业生会被派往世界各地,成为新一代的故事使者。
小丫担任名誉校长,但她坚持每周亲自授课。
那天,她带孩子们去了后山的废弃防空洞??当年父亲藏匿研究资料的地方。洞壁上,仍留着模糊的公式和手绘图纸。
“你们知道为什么声音能穿越时间吗?”她问。
一个男孩举手:“因为它带着感情?”
“对,但还不完整。”小丫点燃一支蜡烛,放在洞口,“声音本身会消散,可当它承载了‘记得’的意志,就会变成一种能量。就像这烛光,看似微弱,却能在黑暗中照亮十年、百年,甚至更久。”
她取出那盘《家书》磁带,放入便携设备。
![[快穿]让反派后继有人吧!](/img/75420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