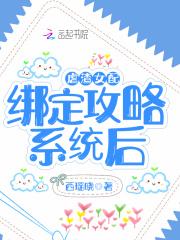笔趣阁>重生七零:开局打猎养家,我把妻女宠上天 > 779文化认同(第2页)
779文化认同(第2页)
她顿了顿,声音更柔:“我想告诉你们,桂花后来嫁人了,但她一直没忘你。她说你写的那封退婚信,她烧了,可话都记着。她说你说‘我不配耽误你’的时候,其实在哭。她也哭了,整整三年不敢听《茉莉花》。”
岩壁微微震颤,仿佛有风吹过,却又不见动静。
片刻后,那个叫“老李”的声音再度响起,这次没有调侃,没有粗话,只剩下一缕沙哑:
>“替我……跟她说声对不起。
>我不是不想娶她,是我怕自己哪天埋在底下,让她守寡。”
念归点头:“我说了,她等这一天,等了六十年。”
话音落下,整条巷道忽然亮起微弱的蓝光,像是萤火虫群聚而来。那些光点缓缓上升,穿过坍塌的矿顶,消失在夜空之中。与此同时,远处传来钟声??不是现实中的钟,而是某种精神层面的共振,唯有她能听见。
她明白,这是他们的执念终于得以释怀。
离开矿井时,东方已泛白。她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废墟,在入口处摆好油灯,又从背篓里取出一面小旗,插在土中。旗面绣着一行字:“此处有光,诸君可归。”
她没有停留太久。下一站是南方一座孤岛,那里曾是麻风病隔离区。几百名患者终生不得离岛,死后骨灰撒入大海,连名字都不曾留下。最近,“心土系统”捕捉到一组异常信号:每逢月圆之夜,岛上广播站的老式喇叭便会自动播放一段童谣,歌词颠倒混乱,却依稀可辨是《两只老虎》。
小满说,那可能是集体潜意识的外溢。
念归决定亲自去看看。
三日后,她乘渔船抵达小岛。码头早已腐朽,木板踩上去吱呀作响。岛上杂草丛生,残破的病房门窗洞开,墙皮剥落,露出斑驳的标语:“战胜疫魔,人人光荣”。她沿着主路前行,忽见一间教室门前挂着块黑板,上面用粉笔写着歪歪扭扭的一行字:
>“今天阳光很好,小美学会了写‘家’字。”
字迹稚嫩,显然是孩子写的。可这栋楼至少荒废了四十年。
她推门进去,屋内桌椅翻倒,课本散落一地。她蹲下身,拾起一本语文书,封面写着“张小美,三年级甲班”。翻开第一页,是一幅蜡笔画:一栋房子,旁边站着三个大人两个小孩,天空飘着红心。
她心头一紧。
这时,窗外传来笑声??清脆、欢快,属于孩童的笑声。
她猛地抬头,只见操场方向,几个模糊的身影正在跳皮筋。他们穿着旧式病号服,脸上戴着口罩,可动作轻盈如风。一个扎辫子的小女孩蹦跳着唱:
>“找啊找啊找朋友,找到一个好朋友……”
歌声戛然而止。
孩子们转过头,齐刷刷望向她。
那一瞬,时间静止。
念归没有退缩。她放下书包,从里面取出十盏迷你油灯,一一摆在讲台上。然后她打开陶片录音机,按下播放键,传出一段经过修复的音频??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某次儿童节演出的实录,节目单上有“合唱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”,可惜原声磁带损毁严重,只剩零星片段。
她轻声跟着哼唱:
>“让我们荡起双桨,小船儿推开波浪……”
奇迹发生了。
那几个身影竟慢慢走近,围在她身边。其中一个男孩怯生生地伸出手,指尖几乎触碰到她的手背。虽无实体,可她感到了温度??微弱却真实,像初春的第一缕暖阳。
小女孩张小美忽然开口,声音细若游丝:“姐姐,我们……可以回家了吗?”
念归泪流满面,用力点头:“可以了。我带你们回家。”
她取出随身携带的名单??那是她这些年整理的“无名者名录”,共三千二百七十一人,涵盖全国数十个被遗忘的角落。她在“张小美”三字旁画了个红圈,轻声念出她的全名:“张小美,生于1963年冬,卒年不详,籍贯浙江宁波。爱好画画,最爱的颜色是红色,梦想是当一名小学老师。”
每念一个名字,岛上就亮起一盏灯。
起初只是她带来的那些,后来,海面开始浮现光点,由远及近,如星辰坠海。渔民们后来回忆,那天夜里,整座岛屿仿佛漂浮在银河之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