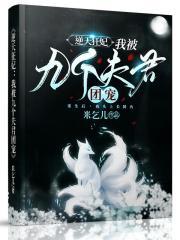笔趣阁>我真没想下围棋啊! > 第四百九十九章 他在支撑着我(第3页)
第四百九十九章 他在支撑着我(第3页)
**“我不怕黑。我只是想让你们听见,我在发光。”**
那一刻,屋外的风忽然停了。
马阿娘跪坐在地,双手合十,嘴唇微动,念着经文。其他孩子纷纷模仿伊布拉的手势,一个接一个打出同样的句子。小小的房间,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光充满。
下午,我们组织了一场“触觉棋会”。每个孩子都可以随意摆放棋子,然后由其他人通过触摸解读情绪。有个六岁的小男孩,把所有白子堆在左上角,形成一团乱麻。他怯生生地说:“那里……是我做噩梦的地方。”
沈砚之蹲下身,轻轻整理那些棋子,改为一片舒展的阵型,然后牵起他的手,放在新布局上:“现在,噩梦散开了。你看,这里有风,有鸟,有阳光。”
男孩笑了,笑得像个终于醒来的孩子。
夕阳西下时,伊布拉找到我们,递来一张折叠整齐的纸。那是他用盲文写的“歌词”,马阿娘帮我们翻译:
>“我没有眼睛,但我记得妈妈的脸。
>她的笑容是暖的,声音是甜的,像夏天的瓜。
>我不知道光是什么颜色,
>但我知道,爱是有声音的??
>它在鼓点里,在手心里,在每一次被人记住的名字里。
>所以,请不要对我说‘可怜’。
>请对我说:‘我听见你了。’”
我把它夹进笔记本,像收藏一颗不会熄灭的星。
临行前夜,马阿娘为我们煮了一壶浓茶。炉火映着她苍老的脸,她说:“这些孩子,从小就被当成废人。村里有人说,瞎子活该被遗忘。可你们来了,带着一块木板、一些石头,却让他们觉得自己……值得被倾听。”
沈砚之沉默良久,从包里取出那副围棋盘,轻轻推到她面前:“留着吧。这不是我们的。它是语言的种子。谁需要说话,谁就能用它。”
她颤抖着手抚摸棋盘纹理,喃喃道:“原来,沟通不需要眼睛,也不需要嘴巴。只需要……一颗愿意靠近的心。”
第二天清晨,我们启程离开。临上车时,伊布拉突然追出来,将一只手工缝制的布袋塞进我手里。里面是一颗打磨光滑的木棋子,刻着一行极小的盲文:**“替我看一次日出。”**
我紧紧抱住他,声音哽咽:“我答应你。”
车子驶离“光明之家”,黄土路上扬起一阵烟尘。后视镜中,那群孩子手拉着手站在校门口,随风挥舞着白手帕。伊布拉站在最前面,脸上带着微笑,仿佛能穿透千里之外的晨曦。
我打开录音笔,轻声说道:
“这里是李砚秋,北京时间三月九日上午八点零二分,甘肃临夏东乡族自治县。今天我们依然没有看到一张完整的眼睑,但我们见证了最明亮的目光。伊布拉教会我,失明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心灵习惯了黑暗,却以为那就是全世界。他说,当他击鼓时,整个宇宙都在共振。”
“我们即将前往内蒙古呼伦贝尔,那里有一群患有自闭症的蒙古族少年,生活在草原深处。他们的父母告诉我们,其中一个孩子三年没说过一句话,但他每天凌晨都会骑马奔向湖边,对着结冰的湖面大声嘶吼??仿佛在跟另一个自己对话。”
沈砚之接过录音笔,望着窗外飞逝的荒原,低声补充:
“别怕说不出话。有时候,最深的语言,恰恰藏在那些无人理解的呐喊里。”
风掠过草原,卷起一缕沙尘,扑打在车窗上,发出细碎的声响。
像鼓点,像心跳,像无数双摸索世界的手,在黑暗中执着地叩问着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