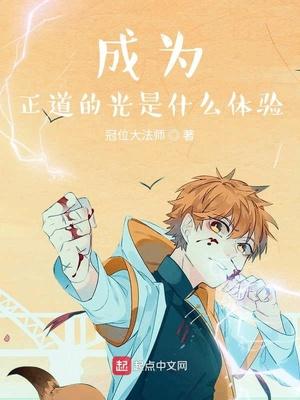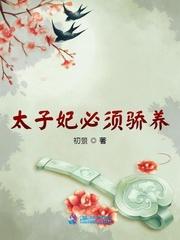笔趣阁>我真没想下围棋啊! > 第五百章 我不知道(第3页)
第五百章 我不知道(第3页)
我站在风中,泪水模糊了视线。录音笔一直开着,里面录下了冰裂声、风声、哭泣声,还有一句我几乎听不清的呢喃??那是巴特尔在沈砚之怀里,用极轻的声音说出的第一句话:
“妈妈……我想回家。”
---
回到“额吉之家”,已是凌晨。我们谁都没睡。乌兰召集了所有孩子,在活动室里点燃了几盏酥油灯。沈砚之把那盘棋复刻在纸上,贴在墙上,然后指着每一手,试图解读巴特尔的情绪。
“第一手白子天元??他在确认自己的存在。”
“黑子小飞挂角??外界的试探。”
“白棋脱先不理??回避沟通。”
“直到中盘那一‘断’??压抑已久的反抗爆发。”
孩子们围坐着,有的摸着棋图复印件,有的闭眼聆听,脸上浮现出少有的专注与共鸣。
突然,一个八岁的小女孩举起手,怯生生地说:“我也想下一盘……我的棋。”
沈砚之点头,递给她一副特制的触觉棋盘。
她叫苏米娅,患有重度语言障碍,只会说几个单字。她低头摆子,速度很慢,但每一手都带着强烈的意图。她把黑子集中在左上,形成一片密不透风的厚势,而白子则零星散布在右边,像是逃亡的孤旅。
“她在画一场暴风雨。”乌兰轻声说,“她三岁时遭遇过草原暴风雪,差点冻死,是她哥哥把她背回来的。”
当黑棋即将吞噬最后一颗白子时,苏米娅突然停住,然后,小心翼翼地在中央补了一手??白子立下,像一棵倔强的小树。
“她不想赢。”我说,“她想活。”
沈砚之握住她的手,在棋盘上写下一行盲文:**“你已经活下来了。”**
苏米娅怔了怔,随即咧嘴笑了,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笑容。
那一夜,我们组织了一场“冰湖之声”分享会。每个孩子都用棋子讲述了自己的故事。有个男孩用“劫争”比喻父母离婚时的拉扯;有个女孩把“双活”解释为“我和影子相依为命”;还有一个总爱啃指甲的孩子,用“弃子争先”形容自己如何学会放弃恐惧。
黎明前,巴特尔悄悄走到我身边,递来一块用牛骨雕刻的小牌子,上面刻着一行蒙文。乌兰翻译道:“他说,这块牌是他名字的印记,送给你,因为你是第一个听懂他喊声的人。”
我紧紧握住那块骨牌,哽咽难言。
天边泛起鱼肚白时,我带着伊布拉的木棋子爬上附近一座小山丘。沈砚之跟在我身后,手里拎着那副围棋盘。我们并肩站着,看着太阳从草原尽头缓缓升起,金色的光芒洒在冻湖上,冰面折射出万千道彩虹般的光带。
我打开录音笔,声音轻却坚定:
“这里是李砚秋,北京时间四月二日上午六点十七分,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。今天,我替伊布拉看了一次日出。光不是颜色,是温度,是声音,是冰裂时的那一声巨响,是十五年沉默后终于出口的一句‘我想回家’。巴特尔教会我,有些语言不需要词汇,只需要一个愿意倾听的耳朵,和一颗不怕破碎的心。”
“这副围棋盘,我们本以为是用来教人下棋的。可现在我才明白,它从来都不是棋具。它是信使,是桥梁,是那些被遗忘的灵魂用来叩门的拳头。”
沈砚之望着远方,忽然说:“下一站,云南怒江。那里有个聋哑学校的围棋兴趣班,老师说,孩子们最近发明了一种‘手势棋谱’,用舞蹈记录每一步棋。”
我笑了:“看来,这盘棋,才刚刚开始。”
风拂过草原,带来远处牧歌的回响。我握紧胸前的木棋子,仿佛听见了千万里之外,伊布拉在鼓上敲出的节拍??
咚、咚、咚。
那是光在行走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