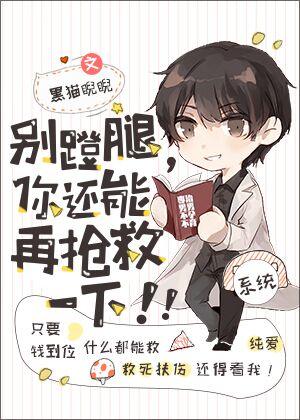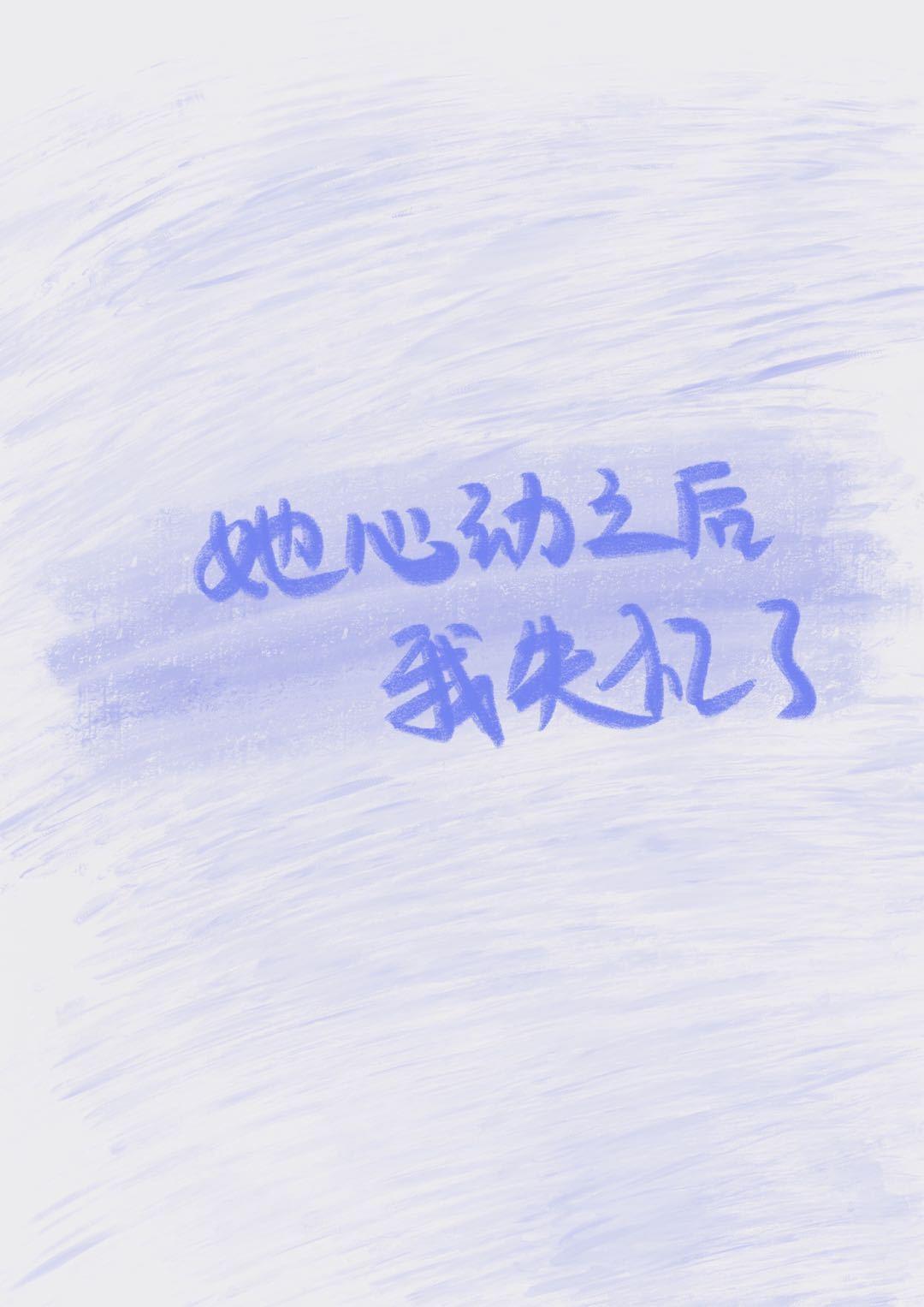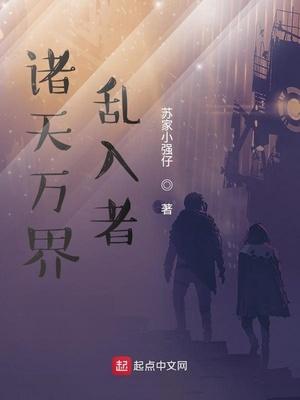笔趣阁>春色满棠 > 第475章 父王最威风小弟也威风(第1页)
第475章 父王最威风小弟也威风(第1页)
小萧翼知道他姐一哭就没完没了。
但他没推开他姐,皱着小眉头,任由他姐抱着他哭。
哭了许久,小公主才松开他,捧着他的脑袋:“父王都瘦了黑了,我看看你瘦了黑了没有。”
边说边把她弟脑袋扭来扭去观察。
确定她弟也瘦了黑了,她难过得捧着她弟的脑袋又哭了起来。
小萧翼被吵得耳膜疼。
他忍了忍,再忍了忍,终忍不了,对他姐说:“我给你带了糖,北月国帝京的特色糖,你要不要吃?”
小公主哭声当即就停了。
小萧翼拿下他姐的手。。。。。。
林小禾站在归名书院的环形花坛中央,手里攥着那张压在门槛前的纸。风从棠树旧址吹来,带着湿润的泥土气息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墨香。她低头看着脚下的石瓮,金叶已尽数沉底,像是一颗颗被埋下的种子,静待破土而出的时刻。
“你知道这瓮里装的是什么吗?”苏晓不知何时走到她身后,声音轻得如同春雨落瓦。
“是……故事?”林小禾试探地问。
苏晓笑了,眼角泛起细纹:“是火种。每一个名字、每一句话、每一次颤抖着说出的真相,都是火种。我们不怕它烧得太旺,只怕它熄得太早。”
林小禾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她忽然想起什么,从书包里掏出母亲给她的一个小布袋,打开一看,是一把晒干的海棠花瓣。“妈妈说,外公临终前只留下一句话:‘我说了一辈子真话,最后换来的是一封检讨书。可我不后悔。’她让我把这些花瓣带来,说它们曾长在他坟头。”
苏晓接过花瓣,轻轻撒入石瓮。花瓣飘落时,竟在空中微微发亮,仿佛吸收了某种看不见的光。她低声道:“你外公的名字,也在‘光名录’上。他是1972年省报编辑部被打成‘右倾翻案’的七人之一。他在狱中写完一本《民间语录辑要》,后来被人偷偷抄录传开。你说的那句话??‘人可以穷,但不能瞎说;人可以死,但不能白死’,就是他写的。”
林小禾怔住了。她一直以为那是妈妈随口讲的故事,没想到竟是外公用命守住的话。
远处传来脚步声,陈砚走了进来,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名单副本。他脸色有些疲惫,但眼神明亮。“刚接到消息,又有四十七个名字通过亲属验证加入‘光名录’。有个老太太从甘肃赶来,带着她丈夫三十年前藏在家谱里的遗书。上面写着:‘若我死于非命,请告诉孩子们,我不是叛徒,我只是不肯举手同意冤枉别人。’”
苏晓接过名单,指尖轻轻抚过那些名字,像是在触摸一个个沉睡的灵魂。“我们原以为最难的是找回名字,现在才发现,最难的是让活着的人愿意承认自己记得。”
正说着,一个男孩跑了过来,满脸通红,像是刚哭过。“老师!我爸爸……他说他不想来!”他是记忆传承营的学生之一,名叫周明远,来自湖南一个小县城。他的父亲原本答应陪他参加闭营仪式,却在最后一刻反悔。
“他说这些事都过去了,提它干什么?还说……还说我不该学这种‘惹麻烦’的东西。”
林小禾听得心里一紧。她想起昨晚在宿舍听到的对话??几个孩子围在一起,分享家人对他们参加这个营的看法。有人说爷爷哭了,有人被母亲责骂“别带坏弟弟妹妹”,还有个女孩低声说:“我爸撕了我的采访笔记,说我再敢问那些事就滚出去。”
陈砚蹲下身,平视着周明远的眼睛:“你爸爸害怕,不是因为他错了,而是因为他还记得。真正忘记的人,是不会生气的。”
“可是……我真的想让他知道,我做的不是错事。”男孩哽咽。
“那就写下来。”苏晓轻声说,“写一封信,不为说服他,只为告诉他:你在听,你在记,你没有忘记他曾沉默过的岁月。”
当晚,孩子们聚在临时教室里,点起蜡烛,开始写信。没有统一格式,没有标准答案,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,像春风拂过麦田。
林小禾写了很久。她先写了外公的故事,又写了今天看到的一切??那朵由灰烬长出的海棠、石瓮中的金叶、水中浮现的文字。最后,她写道:
>“妈妈,我知道你让我来这里,不只是为了听别人的故事。你是希望我能替外公活下去,替他说完那些没说完的话。我会的。我不怕别人说我惹麻烦,因为真正的麻烦,从来不是说出来的话,而是憋在心里一辈子的沉默。”
写完后,她将信折成一只纸鹤,放进书包最里层。
几天后,首届记忆传承营闭幕。三十名学生各自带回了一份整理好的口述史资料、一本《春色满棠》初版书、以及一枚刻有“言”字的铜质徽章。临行前,陈砚站在台阶上对他们说:
“你们带走的不是任务,也不是作业,而是一种选择??选择相信真实比安稳更重要,选择记住比遗忘更勇敢。将来也许会有人笑话你们多事,也许会有亲人责备你们揭伤疤。但请记住:当一个孩子敢于问‘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’,春天就已经来了。”
孩子们陆续离开。林小禾坐上了回乡的班车,窗外青山连绵,阳光洒在田野上,像铺了一层碎金。她靠在椅背上,闭上眼,脑海中浮现出那个清晨的画面??她蹲在书院门前,用石头压住那张纸。
那时她还不知道,自己推开的不仅是一扇门,而是一整个被尘封的世界。
与此同时,在伦敦,艾米丽正站在东方记忆基金会的展厅内,布置一场名为“未寄出的信”的特展。展柜中陈列着上百封泛黄的家书:有母亲写给被遣送下乡的女儿,却始终未寄出的叮嘱;有父亲在劳改营偷偷写下又烧毁的自白;还有一封用铅笔写在草纸上的遗书,末尾画了一个笑脸,旁边写着:“别怕,爸爸只是去种田了。”
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驻足良久,突然伸手触碰玻璃,泪水滑落。“这是我哥哥……他走的时候才十九岁。家里都说他‘自绝于人民’,可我知道,他只是说了句‘粮食不够为什么要开会批斗会计’。”
艾米丽走过去,递上一张印有“光名录”二维码的卡片。“现在,您可以把他找回来了。”
老妇人颤抖着扫码,输入名字。三秒钟后,屏幕上跳出一行字:
>“程志华,1951年生,湖南省醴陵县中学学生。1968年因公开质疑征粮政策失联,2024年经亲属申报确认追念。”
下面附着一段录音??是另一位幸存者口述的回忆:“那天他站在台上,脖子上挂着牌子,脸上全是血。可他还喊了一句:‘我说的是真的!’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