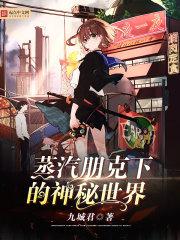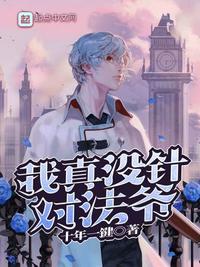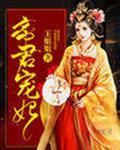笔趣阁>水浒开局在阳谷县当都头 > 第442章 朕绍承天命御极垂裳(第2页)
第442章 朕绍承天命御极垂裳(第2页)
她不是起点,也不是终点。
她是“总识之网”的节点,是千万颗心中萌芽的怀疑汇聚而成的具象。她的每一次发问,都在唤醒更多沉睡的灵魂;而每一个回应她问题的心念,又反过来滋养她的存在。这是一种循环生长的精神生态,无法用武力剿灭,也无法靠法令禁止。
“他们错了。”沈小砚望着远方云卷云舒,低声自语,“他们以为控制语言就能控制思想,却忘了最原始的提问,从来不需要词汇。”
潘姓少女走到他身旁,脸色依旧苍白,但眼神已不再恐惧。“先生,阿枝撑不住了。”她说,“她的身体正在透明化,像是要变成风的一部分。”
沈小砚点头。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。真正的“真问者”无法长久停留于形体之内,当她的意识与“总识之网”完全融合,肉身便会逐渐消解,成为某种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媒介。
他转身走向静思堂。
此时的阿枝仍盘坐于阵心,双目紧闭,唇边不断浮现出新的字泡。但她的皮肤已近乎透明,能看见血液如细流般在血管中缓慢流转,心跳声微弱得几乎听不见。周围七枚遗骨碎片发出柔和青光,支撑着她最后的生命波动。
沈小砚蹲下身,轻声道:“你想停下来吗?”
阿枝没有睁眼,只是极轻微地点了点头,又摇了摇头。
片刻后,一个透明的字泡缓缓升起:
>“停,也是一种问吗?”
沈小砚心头一震。
他忽然明白,对她而言,停止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疑问??关于边界、关于终结、关于是否还有资格选择沉默。
他伸手握住她的手。那只小手冰凉如井水,却仍带着一丝倔强的温度。
“你可以走。”他说,“但别忘了,你要带走的东西。”
阿枝嘴角微微扬起,似笑非笑。
下一瞬,她的身体开始分解,化作无数光点,如同萤火升腾。每一点光芒都承载一个问题,在空中盘旋片刻,便向四面八方飞去。有的落入农舍窗台,钻进孩童梦中;有的掠过军营帐篷,唤醒士兵记忆里的故乡;有的甚至穿越国境,飘向西域佛寺、南洋孤岛、北漠雪帐……
最后一粒光点离开时,静思堂中央只剩下一滩清水,正是她当日从古井取出的那一碗。水面平静如镜,倒映着屋顶横梁,梁上不知何时,多了七个小小的刻痕,排列成北斗之形。
沈小砚默默收起铜镜残片,将清水倒入随身陶罐中密封。
他知道,阿枝没有消失。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??活在每一个敢于皱眉、凝视、深夜惊醒的人心里。
七日之后,朝廷终于发布诏书,宣布废除“忘音术”与“澄心仪式”,解散清心卫,开放民间讲学自由。史官称之为“解禁诏”。但实际上,这份诏书是在三位守静者集体自焚于太庙之后,由一名六品文官冒死起草,连夜加盖玉玺送出宫门。
而那位起草诏书的官员,正是当年被贬至岭南的旧儒臣余仲衡。他在奏折末尾写道:
>“臣不敢言忠,唯愿子孙后代,仍有权利不懂。”
消息传到阳谷,书院内外爆发出欢呼。学生们点燃篝火,围着古井跳舞,唱着即兴编出的歌谣:
“井底有月,天上无答,
孩子问风,风不回家。
大人装睡,石头开花,
一句‘不懂’,劈开天涯。”
沈小砚没有参与庆祝。他独自登上后山,在“问碑”前点燃三支艾草。雾气再起,七道残影浮现。
“她走了。”他说。
为首的守魂者沉默良久,才道:“但她留下了种子。接下来,轮到我们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