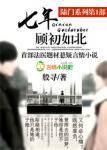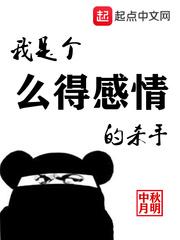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刚想艺考你说我跑了半辈子龙套? > 第487章 全剧组的惊骇欲绝(第2页)
第487章 全剧组的惊骇欲绝(第2页)
收工时,所有人都湿透了,却没人说话。那种寂静,比任何掌声都沉重。
当晚,林默在工作室剪辑样片。画面粗糙,光影斑驳,可正是这份粗粝感,让情感显得无比真实。他把这段剪成三分钟预告片,上传至社交平台,标题写道:
>“他们不是病人,只是迷路了。
>而有些人,愿意走进他们的迷途,陪他们走完最后一程。”
一夜之间,播放量突破百万。
评论区再次涌来无数故事。
有人说:“我爸认不出我妈了,却记得她做的红烧肉。昨天我试着做了一次,他吃了三块,然后看着我说:‘闺女,你妈手艺真像她妈。’”
有人说:“我外婆总问我几点下班,其实我已经辞职三年了。但我每次都答:‘快了,妈,我马上就回来。’我不想让她等不到我。”
还有人说:“你们拍的不是纪录片,是镜子。照出了我们藏在愧疚里的爱。”
林默一条条看完,把它们整理成新的文件夹,命名为“回声?第二辑”。
一周后,《黄昏演员》正式开机仪式在记忆康复中心举行。没有红毯,没有嘉宾致辞,只有林默站在院子里,面对二十多名参与拍摄的护工与志愿者,深深鞠了一躬。
“这不是一部关于死亡的片子,”他说,“而是关于如何活着??哪怕记忆散落如沙,哪怕身份模糊不清,只要还有人愿意回应你的呼唤,你就没有真正消失。”
林秀芬站在人群后排,默默听着,眼眶湿润。
拍摄持续了一个半月。期间,林默几乎住在中心。他学会了帮老人翻身、喂药、擦洗身体,也学会了如何在他们突然哭泣或暴躁时保持镇定。有一次,一位失语老人抓住他的手腕,死活不肯松手,嘴里含糊喊着“女儿”。他没有挣脱,只是轻轻抱住对方,一遍遍说:“我在,爸爸,我在。”
直到老人慢慢放松,沉沉睡去。
那天夜里,他在日记本上写下:
>“原来陪伴是最深的共情。
>它不要求你解决问题,
>只要求你存在。”
影片杀青那天,正好是张桂兰的百日祭。林默带着母带回到殡仪馆,在B-17格位前点燃三支香,轻声说:“张阿姨,我把它带来了。虽然不能在这儿放,但我希望您能听见。”
他掏出耳机,连接手机,播放最后一段成片??那是林秀芬的一场独白戏。
镜头静静对着她,她坐在阳光下的长椅上,怀里抱着张桂兰的旧毛毯。
“有时候我会想,”她缓缓开口,“如果有一天我也忘了我是谁,会不会有人像我对待张阿姨那样,牵着我的手,叫我一声‘妈’?
我不知道。
但我知道,当我握着她的手时,我不是在骗她,也不是在可怜她。
我在完成一场迟到的团圆。
她是我的母亲,我是她的女儿。
哪怕全世界都说这是假的,我们也曾真心相爱过。”
画面渐暗,字幕浮现:
>“谨以此片,献给所有在记忆废墟中依然选择相认的灵魂。”
林默摘下耳机,泪水早已无声滑落。
回到工作室,他收到央视发来的邮件:《被遗忘的名字》播出后引发巨大反响,观众自发组织线下观影会超过两百场,老龄办已决定将“临终陪伴培训计划”纳入年度重点民生项目,并邀请他担任顾问。
他还看到一条私信,来自一位匿名用户:
>“我是当年夕阳居的实习生,看过您的片子才知道,原来张桂兰阿姨每天写的‘老周回来了’,其实是写给她自己看的。她知道自己记不清了,但她不想让‘等待’结束。她说,只要还在等,那个人就还没走。”
林默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,忽然起身翻箱倒柜,找出那封母亲的信。他重新展开泛黄的纸页,逐字阅读那些他曾以为冷漠无情的话语:
>“林默:
>妈不能陪你去艺考,不是不爱你,而是怕你看清我的平凡。
>我只是个小学音乐老师,唱不好高音,跳不动舞步,但我一直记得你说想当演员时眼睛里的光。
>所以我把那束光照进了别人的生命里。
>张桂兰是我同窗,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她病重时托我照顾她记忆里的‘老周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