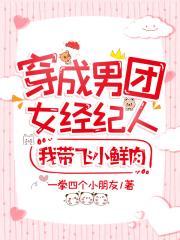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影视编辑器 > 第158章 大明权臣(第4页)
第158章 大明权臣(第4页)
他虽然重视读书,但也深知“耕”是立家之本,从不让孩子们脱离农事。
“顺儿,这锄头的刃要磨利,下地才省力气。”苏守拙一边打磨锄刃,一边教导着儿子。
“知道了,爹。”苏顺用力点头,小脸上满是认真。
堂屋东侧的厢房里,已传来琅琅读书声。
那是长子苏宁,正襟危坐,面前摊开着《大学章句》。
他声音清朗,神态专注。
母亲周氏坐在窗边,就着晨光缝补衣物,听着儿子的读书声,脸上洋溢着满足而平和的笑容。
小女儿秀儿蜷在母亲身边,摆弄着一个布老虎,不时好奇地抬头看看哥哥。
早膳是简单的粟米粥、杂面饼子和一碟咸菜。
饭桌上,规矩却不失温情。
“宁儿,昨日先生讲的《孟子?梁惠王上篇》,可都领会了?”苏守拙抿了一口粥,问道。
“回父亲,儿子已温习数遍,朱子注疏也看了。只是对“仁义与利之辨,尚有些许疑问,准备今日向先生请教。”苏宁放下筷子,恭敬地回答。
“嗯,不懂就问,是好学之道。”苏守拙眼中闪过一丝赞许,随即又看向次子和幼子,“你们也要用心,莫要只顾玩耍,丢了我们苏家的门风。”
“是,爹爹。”苏顺和苏谦连忙应声。
周氏则忙着给孩子们添粥夹菜:“慢点吃,都多吃些。宁儿读书费脑子,顺儿、谦儿下午还要跟你爹去拾柴火。”
她尤其疼爱地摸了摸小女儿的头,“我们秀儿最乖了。”
午后,苏宁前往村中塾学继续攻读。
苏守拙则带着苏顺、苏谦去附近山坡拾取过冬的柴火。
周氏在家纺线、操持家务,小秀儿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母亲身后,偶尔帮忙递个线团。
黄昏时分,炊烟袅袅。
苏宁从学堂归来,带回先生夸奖他文章有进益的消息,苏守拙严肃的脸上难得露出了笑意。
苏顺和苏谦也背着小捆柴火,虽满脸汗水,却兴致勃勃地讲述着在山上看到的趣事。
晚膳比早餐丰盛些,周氏特意炒了一盘鸡蛋,算是给孩子们,尤其是用功读书的苏宁加餐。
饭桌上,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分享着一天的见闻,苏守拙和周氏耐心听着,不时询问或指点几句。
烛光摇曳,将一家人的身影投映在墙壁上,温暖而安宁。
入夜,孩子们睡下后,苏守拙与周氏在灯下低语。
“宁儿是个读书的料子,先生也说他明年院试大有希望。”周氏语气中充满期盼。
苏守拙点了点头,又叹了口气:“希望他能争气,光耀门楣。只是这读书进学,花费不……。。………”
“我省得,”周氏接口道,“我多纺些线,再养些鸡鸭,总能支撑。只要孩子们有出息,我们再苦再累也值得。”
“是啊!”苏守拙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,“耕田是脚踏实地,读书是明理致远。咱苏家不求大富大贵,但求子孙贤德,家宅平安。这便是‘耕读传家”的道理。”
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嘉靖末年,苏家坞这个小小的院落里,却维持着一方难得的和睦与宁静。
父母慈爱,兄弟友爱,姐妹和睦。
对于拥有现代灵魂的苏宁而言,这份质朴而真挚的亲情,是他融入这个时代最温暖的慰藉,也是他未来道路上最坚实的后盾。
另外苏宁深知,明年春天的院试,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前程,更承载着这个耕读之家全部的希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