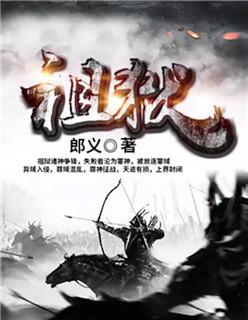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国潮1980 > 第一千六百五十四章 夸张的接机(第1页)
第一千六百五十四章 夸张的接机(第1页)
日本的经济灾难在短时间内所造成的破坏力是惊人的,给日本社会造成的创伤还在持续扩大。
然而日本政府或许是因为出于某些政治层面的考虑,显得颇多顾虑,有些犹豫。
或许也是因为实在有点黔驴技穷,可。。。
夜色如墨,却压不住“承志园”里那一片温润的光。三百支蜡烛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映照着一张张年轻而坚定的脸庞。诵读声渐歇,余音仍缭绕于荷塘之上,仿佛连水中的莲叶都在低语。米晓卉坐在前排,手中那本《灯影之前》已被翻得起了毛边,她将它轻轻合上,指尖抚过封面上父亲留下的印章??“守常”。
就在这静谧时刻,陈知微快步走来,手里攥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文件,神情既惊且喜。“刚刚收到的消息,”她低声说,“国家广电总局联合教育部、文化和旅游部,正式立项‘晨读中国’工程。三年计划,投入专项资金五亿元,目标覆盖全国十万所中小学,每年新增一万所乡村书院,并建立‘民间文化传承人认证体系’。”
李志远闻言站起身,雨水打湿的布鞋还未来得及换下,他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“守常居”主楼,声音微微发颤:“五亿……这不只是钱,是承认。是我们这些人,终于被听见了。”
林婉清坐在轮椅上,由赵振国推着缓缓靠近人群。她抬头望天,今夜无星,但她知道,有些光不在天上,在人间。“当年我父亲常说,教育不是点燃火焰,而是唤醒沉睡的火种。”她轻声道,“如今,火种已成燎原之势。”
消息迅速传开,如同春雷滚过冻土。第二天清晨,全国各地的申请如雪片般飞向“晨读联盟”总部。有甘肃庆阳一位退休语文教师,愿自费筹建“黄土书屋”,只求一套标准诵读教材;有内蒙古草原上的牧民家庭,提出用蒙古包改建“移动晨读站”,随季节迁徙授课;更有广东潮州的一群老匠人联名请愿,要复原宋代“乡学鼓楼”,每日清晨击鼓开读。
最令人动容的,是一封来自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的信。寄信人叫蓝秀兰,是一名聋哑学校的美术老师。她在信纸上画了一幅长卷:一群孩子围坐一圈,手拉着手,口中虽无声,但每个人的手掌都托着一盏纸折的小灯笼,光芒从指尖溢出,照亮整间教室。附言只有短短几句手写汉字:“我们听不见声音,但我们能感受震动。我把诗词编成手势舞,孩子们跟着节奏拍手、踏脚。他们说,这是‘看得见的朗读’。”
米晓卉看完,当即拨通项目组电话:“把她的方案做成示范课,我要亲自去一趟瑶山,帮她把‘无声晨读’推广出去。”
与此同时,“传灯工坊”的老匠人们也迎来了新的使命。江西婺源“敬爱堂”的修缮进入关键阶段,屋顶最后一根主梁需以传统榫卯结构嵌合,不能有丝毫偏差。九十岁的东阳老木匠吴阿公拄拐亲临现场,蹲在泥地上用炭条画图,一边咳嗽一边讲解:“这叫‘三进九出七星斗’,七根短木撑起一根长梁,像北斗护着北极星。咱们修的不是房子,是文脉的脊梁。”
施工期间,一名年轻志愿者不慎将一块雕花窗棂摔裂。众人皆惊,唯吴阿公沉默良久,而后掏出随身携带的一块旧木片??那是他师父六十年前留给他的样品。他亲手将其嵌入破损处,补痕巧妙得天衣无缝。“断了不怕,”他说,“只要心没断,手艺就不会丢。”
这一幕被摄像机完整记录,后来成为纪录片《薪火》中最动人的一帧。
随着“晨读中国”全面铺开,技术力量也开始深度介入。一家科技公司主动捐赠五百台智能诵读终端,内置AI语音识别系统,可实时纠正发音,支持多地方言比对学习。更令人振奋的是,中科院某实验室宣布成功研发“触觉诵读仪”,通过微型振动马达模拟文字笔顺轨迹,盲童只需触摸屏幕,便能“看见”汉字的书写过程。陈默受邀参与测试,当他第一次用手指“读”完一首《登鹳雀楼》时,眼角滑下一滴泪:“原来,我也能看见山河。”
而在新疆和田,“丝路绣读坊”已初具规模。维吾尔族绣娘阿依古丽带领十余名妇女,将《千字文》拆解成四字一句,每一句绣成一幅彩帕。她们用金线勾勒“天地玄黄”,用红丝描绘“日月盈昃”,针脚细密如诗行排列。第一批作品送往北京展览时,竟引发收藏热潮。有人出价十万求购全套,却被阿依古丽婉拒:“这不是商品,是种子。我们要把它送进每一所村小。”
贵州铜仁的吴小川也没让人失望。在他家乡“月亮坪”,第一场露天读书会如期举行。当晚皓月当空,晒谷场上摆了二十几张小板凳,全村老少来了六十多人。十六岁的少年站在中间,手捧那本手抄的《唐诗三百首》,声音清亮: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……”话音未落,一位白发老人突然站起,接过书继续往下念: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接着是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最后全场齐声诵读,声浪穿透山谷,惊起林间宿鸟。
视频传上网后,评论区刷满一句话:“这才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。”
然而,并非所有道路都平坦光明。
四月底,一则新闻悄然发酵:某地教育局以“影响正常教学进度”为由,叫停辖区内所有“晨读十分钟”试点课程。随后,又有几所学校传出压力,称上级要求“不得擅自引入外部教育资源”。舆论一时哗然,支持与质疑并起。有人指责“晨读联盟”借公益之名行文化输出之实;更有自媒体撰文称其“制造情感绑架”,“煽动朴素情怀换取政策红利”。
风波骤起,办公室气氛凝重。陈知微盯着电脑屏幕,眉头紧锁:“这些文章背后,恐怕不止是误解。”
李志远冷笑一声:“当然不止。我们动了某些人的蛋糕。想想看,十万所中小学,每年五亿投入,多少人盯着这块地?一旦变成体制内常规项目,谁来主导?是我们这些草根,还是那些常年盘踞教育系统的‘老面孔’?”
林婉清却异常平静。她取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??那是1938年“烽火读书团”在战火中授课的合影,背景是一堵残破的墙,黑板上写着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。“八十六年前,他们也被骂过‘不务正业’‘空谈误国’。”她说,“可历史记住了谁?记住的是那些在炮火中坚持教孩子写字的人。”
米晓卉点点头,随即拿起手机,拨通央视《文化周刊》栏目组电话:“我想做一次专访。不讲成绩,只讲故事。讲西藏孩子用牦牛毛做灯笼的故事,讲羌族艺人坐着轮椅编竹篱的故事,讲聋哑孩子用手势跳诗词舞的故事。我要让所有人看到,这不是运动,是觉醒。”
专访播出当晚,收视率破纪录。主持人最后问道:“米老师,您觉得这场‘晨读浪潮’,最终想改变什么?”
她望着镜头,眼神清澈而坚定:“不是改变什么,是找回什么。找回我们对文化的敬畏,对知识的虔诚,对每一个普通人发光权利的尊重。我们不是要建一座庙,而是要点千盏灯。每盏灯下,都应该有一个愿意读书的孩子。”
节目结束十分钟后,微博热搜前十中占据六席:“#米晓卉说每盏灯下都该有个孩子#”“#晨读不是形式是信仰#”“#请让月亮坪的读书声继续响下去#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