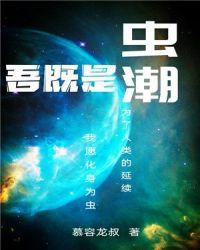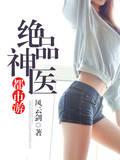笔趣阁>人间有剑 > 第四百三十二章 会过日子(第1页)
第四百三十二章 会过日子(第1页)
听着这话,周迟脸变得有些烫,一时间没说话。
白溪好奇地看着这个家伙,啧啧道:“怎么,咱们现在名震一洲的重云山掌律大人,也会脸红?”
周迟揉了揉脸颊,拿过鱼竿,看向湖面,目不斜视,“也没想过,这大名鼎鼎的白溪会说这种话。”
白溪一屁股坐在周迟身边,一脸理所当然,“你还当我是以前的我?我现在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想说什么,我就说什么。”
周迟看着湖面,点点头,“那很了不起了。”
白溪瞅着那家伙的侧脸,眨了。。。。。。
夜雨初歇,莲林深处雾气氤氲。井畔石阶湿滑如镜,倒映着残月半弯,像一把未出鞘的剑,静静横在天边。小男孩蹲下身,指尖轻触水面,涟漪荡开,那轮残月碎成千片银光,又缓缓聚拢??仿佛天地之间,总有一种力量,执拗地要将破碎重圆。
他已不记得自己何时开始守在这口井旁。或许是那一夜写完最后一句话后,心灯燃起的刹那;又或许更早,在乱葬岗听见阿禾低声说“你还好吗”的那一刻。时间在此处变得模糊,如同井中浮字,来去无痕,却刻骨铭心。
忽然,井水微颤,一圈圈波纹自中心扩散,竟凝成一行新字:
>“有人在等你。”
不是墨迹,也不是金光流转,而是由无数细小的萤火虫拼凑而成,它们从四面八方飞来,绕井三匝,最终定格空中。每一个“字”都是一群生命的聚合,微弱却坚定,像是谁用尽一生力气喊出的声音。
小男孩怔住。
他知道这不是幻觉。这些萤火虫,曾在南疆孩童放飞的纸船上闪烁;曾在北境老兵坟前随风摇曳的铜铃下盘旋;也曾栖落在东海漂远的海藻灯笼边缘,为迷途者引航。它们本不该出现在此地??可如今,却齐聚于此,只为传递一句话:**有人在等你。**
他站起身,望向莲林外的旷野。远处村落灯火稀疏,唯有几盏长明灯仍亮着,那是村民们自发点燃的“心灯”,不分昼夜,只为告诉迷路的人:这里有人守候。
但他知道,等他的不在村中。
他在等一个从未谋面的人,一个名字刻在第七十四块玉牌上、却被世人称为“未知”的人。
也是他自己。
风起了,带着春末特有的暖意与湿润。七十四株新苗簌簌作响,嫩叶翻动间,隐约浮现同样的文字:“我不够好,但我愿意变好。”这句话如今已被抄录千万遍,贴于学堂、军营、牢狱、驿站,甚至敌国皇宫的偏殿之内。有人说它是咒语,能唤醒沉睡良知;有人说它是经文,需静心诵读方可得悟。可小男孩明白,它只是一句最朴素的承诺??就像当年阿禾在雪地里写下“今天,我没偷东西”那样简单而沉重。
他闭上眼,耳边响起无数声音。
疯癫老尼撕下旧恨时的决绝;刺客蒙面行医时低哑的“我还好吗”;渔妇放灯入海时温柔的“只要有人愿接”;蓝绳叔叔系上铃兰花绳时爽朗的笑……还有那百岁校长颤抖的手势、“无声学堂”七十四双承接月光的手掌、壁画中千万张含笑的面孔……
所有声音汇成一条河,流淌在他血脉之中。
他睁开眼,提笔。
这一次,不是写在纸上,也不是投于井中,而是悬于半空,以铃兰花茎为笔,以天地为纸,一笔一划,倾注全部心意。
>“我来了。”
三个字落下,萤火虫骤然散开,化作漫天星雨,融入夜色。紧接着,远方传来脚步声??很轻,很慢,踏在泥泞之上,带着疲惫,却无比坚定。
一道身影穿过薄雾走来。
布衣草履,面容清癯,手中握一朵铃兰花。正是那年春分留下话语后悄然离去的铃兰客。
但这一次,他不再是孤身一人。
他身后跟着七个人,衣着各异,神情不同,却都佩戴着玉牌。
第一位是少女孙女,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妇,手中提一盏油灯,火苗跳跃如初见那天。
第二位是西北戈壁医馆的主人,依旧蒙面,只露出一双眼睛,深如古井,却映着暖光。
第三位是东海“蓝绳叔叔”,腕上缠满褪色蓝绳,每一条都系着一个孩子回家的路。
第四位是南疆失明幼童的母亲,怀中抱着一名婴儿,襁褓之中,静静躺着一朵铃兰花。
第五位是北境桃林摘果的孤儿之一,肩扛桃枝,铜铃轻响,似与百年老兵遥相呼应。
第六位是十三州“无声学堂”的现任校长,双手完整,却坚持用手语交流,掌心始终向上。
第七位,则是个陌生少年,满脸风霜,眼神清澈,胸前玉牌刻着两个字:“小满”。
他们一步步走近,没有言语,只是站在铃兰客身后,静静望着井心。
![非典型求生欲[快穿]](/img/42405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