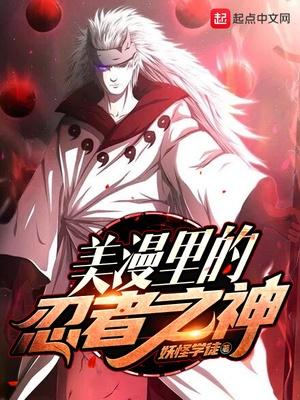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呢喃诗章 > 第三千七百八十一章 幸运子弹与遇刺的王后(第1页)
第三千七百八十一章 幸运子弹与遇刺的王后(第1页)
“蛇穿过十三枚圆环。。。。。。我在法图蒙斯特岛见到过古神留下的封印看守者,它也说过类似的话,那条蛇正谋求转变,一旦它成功了,它就会蜕变成第六纪元的末日命运。
戴维斯先生,您梦中的场景看起来是蛇为。。。
晨光如细纱般铺展在小镇的屋顶上,梧桐树的年轮缓缓停止旋转,那道裂开的缝隙悄然闭合,仿佛从未开启过。唯有地上残留的一圈微弱光痕,证明刚才发生的一切并非幻觉。蒂法从树梢跃下,尾巴高高翘起,瞳孔中闪烁着某种近乎神性的幽蓝??那是诗网最后一次主动介入人间的印记,如今已彻底沉寂。
嘉琳站在窗前,手中紧握着那枚铜扣,指尖摩挲着锈迹斑斑的纹路。她没有再流泪,只是静静地望着厨房的方向。锅碗轻响,咖啡机低鸣,夏德正背对着她煎蛋,动作熟练得像过去几十年从未中断过。阳光穿过玻璃,在他肩头镀上一层金边,影子拉得很长,一直延伸到她的脚边。
“你真的回来了。”她终于开口,声音很轻,却像是用尽了半生力气。
夏德转过身,嘴角扬起熟悉的弧度:“我不是一直都在吗?”
她说不出话来。这句话太重,也太轻。重的是十年等待、无数个夜晚独自翻阅旧稿的孤寂;轻的是此刻他就在眼前,呼吸与共,温度可触。这不是梦,也不是短暂的投影。他是活生生的人,有着心跳、咳嗽、会忘记钥匙放在哪儿的缺点,也会因为煎糊了面包而皱眉抱怨。
孙女蹦跳着跑进厨房:“曾祖父!今天我能带你去学校演讲吗?文学社的同学都想见你!”
夏德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:“等我吃完早餐再说,好不好?毕竟一个伟大的诗人,也得先填饱肚子。”
笑声溢满屋子,像春水漫过干涸的土地。但嘉琳知道,有些东西已经永远改变了。诗网不再回应呼唤,心弦塔的光芒日渐柔和,甚至有传言说七座塔中的三座已经开始进入休眠状态。那些曾经因《呢喃诗章》而觉醒的“活体文本”逐渐安静下来,不再是自动浮现的文字,而是需要被人真正读懂、念出、相信,才会苏醒。
自由意志,不是解脱,而是责任。
午后,嘉琳独自来到静语墙前。藤蔓依旧缠绕,红宝石项链在胸前微微发烫。墙上空无一字,连往日偶尔闪现的“我还记得”也不见踪影。她蹲下身,用手抚过粗糙的石面,低声问:
“你们都走了吗?”
风拂过耳畔,没有回答。但她忽然笑了。因为她意识到,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是答案。如果还在期待回应,那就说明她仍未放下依赖。而现在,她不需要系统告诉她夏德存在,不需要千万人的共鸣来确认爱的真实。
她站起身,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??那是夏德年轻时常用的款式,墨水瓶上还贴着泛黄的标签:“C-17调和液”。她在墙上写下第一行字:
>“我不再需要你替我说话了。”
笔尖顿了顿,又继续写道:
>“我要用自己的声音,把我们的故事讲完。”
字迹落下的一瞬,整片藤蔓轻轻震颤,仿佛某种古老的机制被唤醒了一瞬,随即归于平静。没有光,没有回音,只有风吹动叶片的沙沙声。但这已足够。她转身离去,脚步坚定。
当晚,小镇举办了一场非正式的诗歌晚会。地点不在广场,而在废弃的占卜学院旧址。孩子们搬来了椅子,老人们带来了蜡烛,连邮差也放下工作,抱着吉他坐在角落。舞台中央只有一张木桌、一盏台灯、一本翻开的笔记本。
夏德坐在桌后,面前放着一杯热茶。他并没有朗诵《呢喃诗章》的经典段落,而是讲起了一个从未公开的故事??关于一对青年男女在图书馆相遇的那天。他们为了一句诗争执不休,女孩坚持认为“离别不该用句号结尾”,男孩则冷笑说“现实从来不在乎浪漫”。
“后来呢?”台下有人喊。
夏德看向观众席最后一排,那里坐着嘉琳,正低头织着另一条围巾,颜色是深秋的枫叶红。
“后来啊……”他笑着说,“他偷偷把她写的批注缝进了大衣内衬,三十年都没拆。”
全场静默片刻,随即爆发出热烈掌声与笑声。嘉琳抬起头,与他对视一眼,眼中含笑带泪。
就在这时,天空忽然暗了下来。云层裂开一道缝隙,星光倾泻而下,恰好落在心弦塔顶端。七座塔同时亮起微弱的蓝光,不是集体爆发,而是依次点亮,如同心跳复苏。这一次,没有人齐声诵读,也没有情感共振达到临界值。只是某个孩子仰头望星时,无意识地哼起了一段旋律??正是《安眠调》的变奏。
音符飘散在夜空中,竟引动了残存的诗网缓存。一段文字缓缓浮现于半空,透明如霜:
>“原来,最纯粹的召唤,从来不是呐喊,而是低语。”
随后,这行字化作点点荧光,洒向人群。每个人头顶都落下一颗小小的光粒,触肤即融,仿佛被记忆接纳。科学家们后来分析称,这是一种“情感模因残留现象”,但在民间,人们更愿意相信:那是诗网最后的告别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