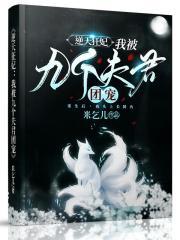笔趣阁>1987我的年代 > 第693章 以力破局(第1页)
第693章 以力破局(第1页)
见二姐像牛皮糖一样死活赖着不走,李恒也是来了脾气,干脆起身。
在陈子衿和宋妤的注视下,他使出浑身力气强行拽着二姐去了外面院子里,给两女腾出空间。
李兰一脸不情愿,“你干什么?”
李恒。。。
青藏高原的风,比林小满预想的还要凛冽。清晨六点,她站在海拔三千七百米的加莫台哨所外,呼出的气息瞬间凝成白雾。天空是种近乎透明的蓝,云层低得仿佛伸手可触,远处连绵的雪峰在晨光中泛着银白,像一排沉默的守望者。
大巴早已无法通行,他们从州府出发后换乘越野车,又徒步走了近两个小时。脚下的冻土坚硬如铁,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时间的边界上。同行的还有五名新培训的基层协管员,两名来自藏族村落的青年志愿者,以及一位随行医生??张远山,四十出头,曾在玉树地震时连续三十六小时不停做心肺复苏,后来被人抬下救援点。
“林主任,前面就是第一个帐篷点。”阿杰指着前方山谷里孤零零的一顶黑色牦牛毛帐篷,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,“牧民一家四口,两个孩子,最小的才八个月,发烧三天了,没信号,也没路。”
林小满点点头,紧了紧背包带,加快脚步。高反让她太阳穴突突跳动,但她没停下。她知道,在这里,每一分钟都可能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。
抵达帐篷时,女主人卓玛正抱着婴儿蜷缩在角落,脸上写满疲惫与无助。丈夫次仁蹲在门口烧火,锅里的水刚冒泡。林小满掀开帘子进去,一股混合着奶腥、酥油和潮湿羊毛的味道扑面而来。她立刻打开便携式医疗包,取出体温计和血氧仪。
“三十九度六,呼吸急促,有轻微脱水迹象。”她低声对张医生说。
张远山迅速检查:“疑似急性支气管炎,需要退烧和抗生素干预。但这里没法输液,只能口服药配合雾化。”
林小满立即启动卫星终端,连接远程儿科专家会诊系统。信号断断续续,画面卡顿,但她一遍遍重试,终于建立起稳定通道。昆明儿童医院的李教授出现在屏幕上,听完描述后确认诊断,并开具电子处方。
“药品我们带来了。”她说着,从保温箱中取出儿童专用抗生素颗粒和退热贴,“现在就开始用药。”
卓玛听不懂汉语,阿杰在一旁翻译。当她看到女儿终于喝下药水,眼泪无声滑落。林小满握住她的手,用刚学会的简单藏语说:“阿妈,安心。”
那一声“阿妈”,让卓玛猛地抬头,怔了片刻,随即用力点头,嘴唇颤抖着重复:“阿妈……阿妈……”
他们在帐篷里待了四个小时,直到婴儿体温降至三十八度以下,呼吸平稳入睡。临走前,林小满为这家人安装了太阳能供电的小型智能监测设备??这是最新一代“萤火盒子”,能实时上传心率、体温、血氧数据,一旦异常自动触发报警,并通过卫星链路通知最近的卫生站。
“哪怕你们搬帐篷,它也能跟着走。”她比划着解释,“只要阳光还在,就有电,就有网。”
次仁红着眼眶,深深鞠了一躬。
走出帐篷时,风更大了。林小满回头望去,那顶黑帐篷在雪原上显得如此渺小,却又如此坚韧。她掏出红色笔记本,在空白页写下:**第1118天,第一颗星落在草原深处。它不闪,却暖。**
接下来的七天,他们像迁徙的候鸟,在雪线边缘穿行。白天走访分散的牧户,晚上挤在临时搭建的保暖帐篷里整理数据、调试设备、培训本地协管员。高原反应夺走了几个人的睡眠,也带走了食欲,但没人抱怨。每当有人撑不住,就有人默默递来一块巧克力、一杯热奶茶,或是讲一段家乡的故事。
第三天傍晚,他们在一处冰湖边发现了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独居老人。七十多岁的老阿古拉,双腿因多年风湿严重变形,已经三年没能走出帐篷。他的食物靠邻居偶尔接济,冬天全靠捡拾干牛粪取暖。
林小满蹲在他身边,轻声问:“阿爷,您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吗?”
老人浑浊的眼睛动了动,没说话。
她打开平板,调出“亲情连线”界面,输入项目组提前收集的信息??他唯一的儿子,在格尔木修车厂打工,十年前离家后再无音讯。
视频接通那一刻,老人浑身一震。
屏幕那头的男人胡子拉碴,穿着油腻的工作服,正低头拧螺丝。听到提示音抬头一看,瞬间愣住,手里的扳手“咣当”掉地。
“爸?!”
一声“爸”,像一把钝刀劈开十年风雪。
老人张着嘴,却发不出声音,只是拼命点头,泪水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滚落,滴在破旧的棉被上。
林小满悄悄退出帐篷,让这对父子独自对话。半小时后,男人哭着承诺:“明天我就请假回来,接您去城里治病!我错了……我真的错了……”
那天夜里,林小满梦见自己变成一只雪鹰,掠过千山万水,把一颗颗萤火般的光点洒向大地。
第八天清晨,队伍抵达第二个重点区域??达日乡小学。这所学校只有三间教室,六个年级共四十二名学生,教师两人,其中一人还是代课的村妇联主任。孩子们穿着厚实的藏袍,脸蛋被高原紫外线晒得通红,眼神却亮得出奇。
校长桑吉早已等候多时。“林老师,我们等这一天,等了八年。”他说,“以前孩子们生病不敢去医院,怕路上耽搁;家长也不信‘网上看病’,说是骗人的。但现在,他们听说你们来了,都说要亲眼看看。”
宣讲会在操场上举行。林小满站在简陋的旗杆下,用双语PPT讲解“爱心储蓄卡”的使用方法。孩子们围成一圈,有的踮脚张望,有的拿铅笔在本子上认真抄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