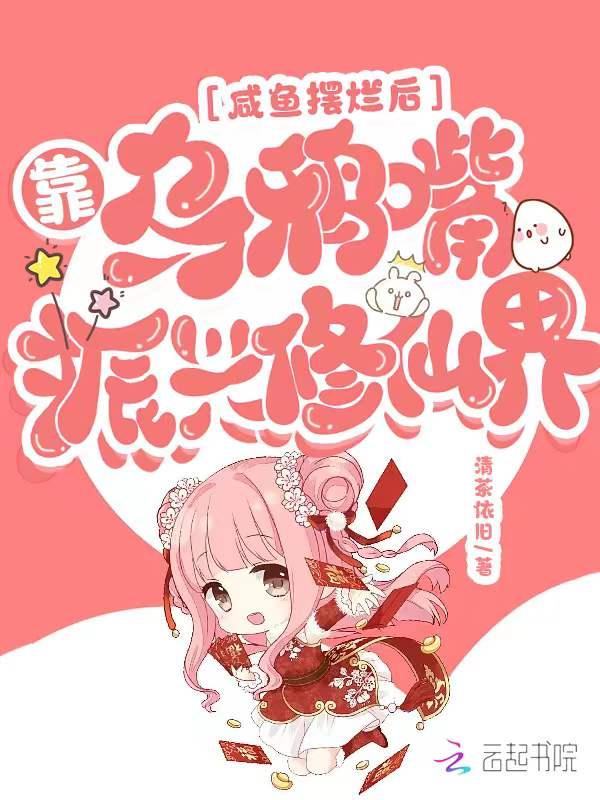笔趣阁>皇修 > 第1235章 欲抛(第2页)
第1235章 欲抛(第2页)
里面传来多年前身陷战火的母亲的声音:“昭儿,妈妈不怕死,只怕你将来活得不像自己。记住,无论世界多么吵,你要听清心里那个最小的声音。那是你最初的模样。”
泪水无声滑落。
他知道,自己也曾逃避过。当年拒绝认回陈砚,不仅仅因为他是战争策划者,更因为他害怕一旦接纳那段血缘,就会动摇自己坚持正义的纯粹性。可母亲说得对??爱是选择。恨可以存在,但不必吞噬全部生命。
他打开手机,拨通国际刑警组织预留的专线。
“我想见陈砚。”他说,“条件由你们定,地点也可以不在圆环内。但我希望,是以儿子的身份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,才回应:“他还活着,在格陵兰海底监狱。精神状况不稳定,最近频繁提起你的名字。我们会安排转运,但需签署风险协议。”
挂断后,他又录下一段话,存入录音笔:
“爸,我不知道该怎么叫你。我恨你下令轰炸平民村庄,也记得你教我辨认星星时的笑容。如果你愿意说真话,我想听。不一定是为了宽恕,只是为了……不再逃。”
春天来临之时,第三十九个圆环在格陵兰建成。它位于极昼永不落幕的冰原之上,建筑材料全部采用回收金属与再生木材,象征终结与重生的交织。
陈砚被带入时,已年过八旬,脊背佝偻,双手颤抖。他曾是掌控百万军队的战略家,如今连走路都需要搀扶。陆昭坐在对面,两人之间仍是那碗清水,映着永恒的日光。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活到现在吗?”陈砚开口,嗓音干涩,“不是因为他们仁慈,是因为我掌握太多秘密。每一个情报网、每一处暗杀据点、每一份未公开的战争档案……他们都想从我嘴里挖出来。可我一直不说,因为我怕,一旦交代清楚,就连最后一点存在的价值也没了。”
陆昭静静听着。
“直到前几天,我在牢房里做了个梦。”老人闭上眼,“梦见一个小女孩站在焦土上,手里攥着半块烧糊的饼干。她说:‘叔叔,你能抱抱我吗?我妈妈再也抱不动了。’然后我就醒了,哭了整整一夜。那是我下令轰炸的村庄里的孩子……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。”
他抬起浑浊的眼睛:“儿子,我犯下的罪,无法用一生赎清。但如果你还愿叫我一声‘爸’,我想试着做一个配得上这个称呼的人。”
陆昭喉头滚动,终是起身,绕过水碗,走到他面前,轻轻抱住这位垂暮的老人。
没有言语,只有呼吸交织。
窗外,极光如绸缎般铺展天际,仿佛整个宇宙都在见证这一刻。
数月后,陈砚主动提交了长达三千页的战争罪行自述,并附上全部机密坐标。数十个国家据此展开追责行动,百余座隐藏军事设施被揭露,数千名逍遥法外的战犯落网。
他在完成最后一份口供当天去世,遗嘱只有一句:“请把我葬在格陵兰圆环旁,面朝南方??那里有我儿子站着的地方。”
葬礼那天,全球二十四座运转中的圆环同时静默一分钟。无数人在黑槐树下低头,为一个曾经制造恐惧的灵魂送行。
陆昭站在坟前,放下一片紫叶。
他知道,这不是终点。未来仍会有新的谎言滋生,旧的伤痛复发,制度会被滥用,理想会变质。但他也开始相信,只要还有人愿意在真相面前弯腰,还有人敢于在仇恨中伸出一只手,这个世界就仍有缝合的可能。
某夜,他在日记中写道:
>“我们曾以为,说出真相是最勇敢的事。
>后来才发现,真正的勇气,是在听完真相后,依然选择靠近对方。
>不是为了遗忘,不是为了赦免,
>而是因为,我们都曾是那个躲在谷仓顶上、不敢呼救的孩子。
>也都渴望有人听见,然后说:
>‘我在这里。’”
翌日清晨,新一批志愿者抵达高原营地。他们来自不同国家,肤色各异,有人带着创伤,有人怀着疑问。陆昭迎上前去,带领他们走向那棵历经风雨的问树。
嫩芽正不断抽出,每一片都比前一代更深邃,脉络中隐隐流动着银光,宛如承载了亿万未曾熄灭的心跳。
风起时,树叶沙响,如同无数低语汇成一首歌。
他仰头望着,嘴角微扬。
轮到我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