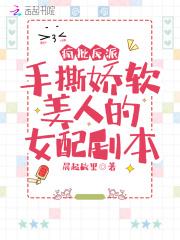笔趣阁>激荡1979! > 第494章 魏平安 谁是爹来谁是儿(第1页)
第494章 魏平安 谁是爹来谁是儿(第1页)
离开香港之前龚?还去了一趟青鸟公司,跟夏梦女士说明自己出国的事,不过开机时间定在九月份,肯定不会耽误正事的。
夏梦也表示了恭喜:“那你父母要跟着一起去吗?”
龚?摇摇头:“我那个侄子还有堂。。。
夜深了,孟波仍坐在电脑前,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,像一层薄霜。他刚把阿水婆的语音又听了一遍,那句“只要人心不倒,旗就不会落”在他心里来回撞击,像潮水拍打礁石。窗外风起,树叶沙沙作响,仿佛有无数低语从远方传来。
他打开录音笔,翻出最近一次在浙江嵊州采集的声音??那是八十六岁的俞秀英,曾经是新中国第一批女子测量队成员。她们背着六分仪和水准仪走遍浙东山区,为铁路选线踏勘。老人说话慢,但字字清晰:“那时候没人信女人能干这活。我们白天爬山测数据,晚上在油灯下画图,手冻得握不住笔,就哈口气暖一暖。有一次暴雨冲垮了山路,我们五个人用身体搭人桥,让仪器先过去。”
录音里还有一段她哼的小调,是当年队里传唱的《山高水长》:“山再高,踩在脚下;水再急,挡不住咱。姑娘们的脚印,刻进大好河山……”
孟波闭上眼,耳边突然响起另一种声音??是挖掘机轰鸣、钢筋碰撞、混凝土浇筑的工地杂音。他猛地睁开眼,意识到那是1979年春天的记忆。那一年,他在上海读大学,亲眼看见外滩边第一座高层建筑破土动工。那时人们说:“新时代来了。”可谁还记得,在这片土地上,早已有无数女人用脚步丈量过荒野,用双手开垦过冻土?
他起身走到书架前,抽出一本泛黄的《中国妇女运动简史》,翻到1958年那一章。上面写着:“全国掀起‘妇女能顶半边天’热潮,大批女性投入水利、交通、能源建设。”可再往下读,具体的人名寥寥无几,大多以“某地妇女突击队”一笔带过。
“这不是遗忘,是系统性抹除。”他低声说。
第二天清晨,团队启程前往黑龙江漠河。他们要去寻找一位叫李桂芬的退休气象员。根据线索,她是1960年代唯一一名常年驻守北极村观测站的女职工。零下五十度的极寒中,她独自记录气温、风速、降雪量整整十二年,从未中断一天。
通往北极村的路被大雪封了三天,直到第四天才勉强通车。车轮碾过冰壳,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,像踩在骨头之上。沿途村庄稀少,偶尔能看到木屋烟囱冒着青烟,狗吠声穿透雪雾。
抵达时已是傍晚。李桂芬拄着拐杖站在门口,穿一件旧军大衣,头戴毛线帽,眉梢挂着霜。她见到摄制组,并未多言,只点点头:“进来吧,屋里暖和。”
屋内陈设极简:一张床、一个炉子、一张桌子,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地图,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几十年来的极端天气数据。最引人注目的是角落里的那个老式气象箱,玻璃罩下放着一支温度计、一个气压表、一本写满数字的日志。
“这是我的命。”她说,“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开窗测温,雷打不动。哪怕手指冻僵了,也要记下来。因为这些数据,关系到整个东北的防灾预警。”
她翻开日志,指着1972年1月的一行字:“-52。3℃,创历史极值。”那天她差点死掉。“凌晨四点去取样,风太大,门被吹飞了。我追出去,脸立刻结了一层冰。回来时鼻子掉了块皮,眼睛睁不开。但我还是把数据抄完了。”
“为什么非得是你?”小王忍不住问,“就不能换个人吗?”
李桂芬笑了,眼角皱纹堆叠如沟壑:“当时没人愿意来。男人嫌太苦,女人更不敢来。领导问我敢不敢,我说,我姓李,不怕冷。”
她顿了顿,声音轻了些:“其实我也怕。怕黑,怕狼,怕半夜听见风声像鬼哭。可我知道,如果我不来,这个站就得撤。一旦撤了,下次再建,就不知道要等多少年。”
她说起曾有个年轻男同事来支援,待了三天就哭了,求着调走。“临走前他说:‘姐,你真是铁打的。’我说我不是铁打的,我只是答应过组织,也答应过自己??既然来了,就不能退。”
当晚,他们在炉边整理素材。孟波忽然发现,李桂芬的日志本末页夹着一张照片:三个年轻女子并肩而立,穿着棉袄,戴着雷锋帽,背后写着“1963年全国气象工作者合影”。其中一人正是李桂芬,旁边两位却陌生得很。
“另外两人呢?”他问。
李桂芬沉默良久,才开口:“一个叫王玉兰,在内蒙古测暴风雪时滑下山坡,没了。另一个叫孙秀珍,文革期间被批斗,说是‘假专家’,逼她承认篡改数据。她不肯,跳井了。”
她的声音很平静,仿佛在讲别人的事。“后来我每年清明都寄花圈,写她们的名字。可没人知道她们是谁。档案里只有编号,没有生平。”
孟波心头一紧。他又想起四川那位吉克阿依,想起甘肃马金花,想起云南陈秀兰……这些女人,她们不是没有名字,而是名字从未被郑重念出。
第二天,摄制组提议在观测站原址举行一场小小的纪念仪式。他们带来两块铜牌,分别刻着王玉兰和孙秀珍的名字与生卒年月。当李桂芬亲手将它们钉在木柱上时,天空飘起了雪。
雪花落在铜牌上,渐渐覆盖了字迹。但她没擦,只是望着远方:“没关系,雪会化,字还在。”
返程途中,孟波接到电话??国家档案局同意开放一批尘封的“三线建设”女性职工档案。这批资料涉及川、贵、陕等地军工、地质、通信系统的万名女工,时间跨度从1964年至1980年。此前因涉及保密条款,长期未能公开。
“我们可以进去看吗?”他问。
“可以,但只能抄录,不能拍照,且每日限阅两小时。”
一周后,北京西郊某地下档案馆。厚重铁门开启时,一股陈年纸张混合樟脑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成排铁柜延伸至幽暗深处,宛如墓道。
负责接待的老管理员姓周,七十多岁,曾是当年档案室的值班员。他带着他们走进B区第十七排,“这里全是女工登记表。你们想找什么样的?”
“所有参与野外作业、高空作业、高危岗位的。”孟波说。
周老头点点头,拉开一个抽屉。里面是一摞泛黄的卡片,每张正面贴着黑白证件照,背面写着姓名、籍贯、文化程度、健康状况、政治表现……
第一张照片上的女孩约莫二十岁,齐耳短发,笑容腼腆。姓名栏写着:刘慧敏,江苏苏州人,高中毕业,分配至贵州某雷达站,负责高空架线。备注栏有一行小字:“1967年因雷击殉职,年二十一。”
第二张:张丽华,河北保定人,初中学历,地质勘探队员。备注:“1971年探洞坠亡,遗体七日后寻获。”
第三张、第四张……几乎每十张就有一张写着“死亡”“失踪”“病退”。
“这些人,都没评烈士?”小王声音发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