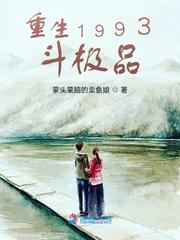笔趣阁>我爹是崇祯?那我只好造反了 > 第四百四十七章 既然有争议那就再加一场考试吧(第1页)
第四百四十七章 既然有争议那就再加一场考试吧(第1页)
暖阁内,气氛凝重得几乎能滴出水来。
炭盆中的银炭依旧散发着融融暖意,但此刻这暖意却丝毫无法驱散弥漫在空气中的冰冷与压抑。
薛国观带来的消息如同沉重的巨石压在在场每个人的心头。
学子聚。。。
风过檐角,铜铃轻响。柳含烟望着那轮初升的朝阳,指尖微微一颤,仿佛还残存着三日前地火爆发时的灼热。她低头看了看朱慈?的手??那曾执笔批阅万机、也曾握剑斩佞除奸的手,如今枯瘦如柴,却仍紧紧攥着她的掌心,像抓住最后一缕生还的希望。
“你说得对。”她缓缓开口,声音低得几乎被风吹散,“我们不是什么‘真’帝后。你本不该是皇帝,我更不是皇后。可这江山,却是我们一寸一寸抢回来的。”
朱慈?轻轻笑了,嘴角牵动伤口,疼得皱了皱眉。“你知道吗?我在南方流浪那十年,睡过破庙,吃过狗食,被人骂作‘假太子’,也被人当成灾星驱逐。可每当我想放弃时,总有个念头撑着我??若我不站出来,谁来替那些饿死在路边的孩子说话?谁来烧掉户籍册上‘贱籍’二字?谁来让一个女子也能堂堂正正走进学堂?”
他顿了顿,目光望向远处宫墙外熙攘的街市:“我不是为了龙椅而活。我是为了他们。”
柳含烟眼眶微热。她想起昨夜太医院奏报:陛下左臂经脉尽断,恐终生无力执笔;右肺被烟尘灼伤,每逢阴雨便咳血不止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,在火海将塌之际,竟拼死扑向祭坛深处,只为推开她,自己引爆炸药封住火髓井口。
“你何必……”她当时嘶声喊出的话,终究没能问完。
因为他早就知道答案。
真正的帝王,不在血脉,不在玉玺,不在史书上的名号。而在民心所向,在万家灯火,在百姓口中那一声发自肺腑的“皇上”。
此刻,坤宁宫外传来脚步声。一名小宦官捧着厚厚一叠奏章快步而来,神色恭敬:“启禀监国夫人,各部急报已汇齐。”
柳含烟起身接过,翻开第一本,便是兵部孙传庭亲笔密奏:
>“赫图阿拉废墟清理完毕,共掘出尸首一百七十三具,其中确认魏忠贤遗骸,头颅碎裂,应系坍塌时巨石砸中致死。其贴身铁匣内藏《癸未雪鹰录》终卷,内容为双生子养育计划全案,附当年稳婆供词及接生图谱,现已封存待审。”
>
>“另,秦翼明率残部寻获失踪锦衣卫骆养性,其人被困冰窟七日,冻去一足,然神志清明,已带回京诊治。据其所述,吴三桂私通敌军确凿,现已被押入天牢,等候发落。”
>
>“辽东诸部震动,原附逆之蒙古三部遣使请降,愿归顺大明,纳贡称臣。惟建州残余势力退入深山,尚有零星活动,已命祖大乐继续清剿。”
她一页页翻看,眉头渐松。忽然,一张夹在奏章中的泛黄纸片滑落。拾起一看,竟是半幅孩童画像,墨色陈旧,边角焦黑,似从大火中抢出。画中两名幼童并肩而立,容貌几乎一模一样,唯有左侧孩童胸前隐约绘有一道飞鹰状红痕。
背面题字,笔迹苍劲:
**“天启八年冬,周皇后双诞龙裔,皆为亲出。奉天承运,非人力所能篡。然一入江湖,一堕权谋,终成两世因果。老臣骆思恭泣血记。”**
柳含烟怔住良久,终将画像贴于胸口,闭目不语。
这时,朱慈?轻声道:“把这画挂起来吧。不是挂在乾清宫,而是挂在国子监的大殿上。让天下读书人看看??所谓正统,并非天生注定;所谓真假,须由万民评判。”
她点头,唤来内侍,命其速送国子监监正,附旨一道:“此画名为《双生图》,即日起列为大明治国镜鉴,凡入学士子,必观而思之。”
午后,春雷隐隐,细雨洒落宫瓦。柳含烟独自步入皇史?,这座存放皇家典籍的石室常年阴冷,今日却多了一盏长明灯。她走到最深处的铁柜前,取出一只紫檀木匣,打开,里面静静躺着三样东西:一枚残缺玉佩、一瓶漆黑如墨的“九幽引”,以及一封未曾拆封的信。
信封上写着:“若吾死,交予含烟亲启。”
是骆思恭的笔迹。
她颤抖着手撕开封口,展开信纸,只读了一句,泪水便夺眶而出。
>“吾一生效忠皇室,查案千起,唯此一事,愧对天地。当年未能护住双生皇子,致使骨肉分离,权阉弄局,实乃毕生之耻。然今见陛下以仁政治天下,夫人以铁血守江山,方知天道虽迟,终不亡善。此身虽朽,魂当安矣。”
信末附有一行小字:“雪鹰已落,真龙归心。愿后世子孙,永不再问‘你是谁’,而只问‘你为何而治’。”
她跪坐在地,抱着木匣痛哭失声。三十年风云变幻,多少忠魂埋骨,多少阴谋织网,多少人在黑暗中默默燃尽自己,只为换来今日这一线清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