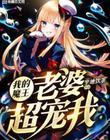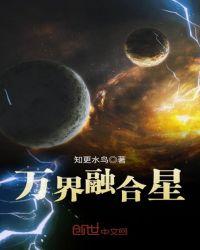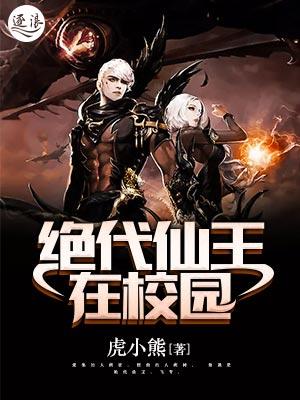笔趣阁>谁说这顶流癫!这顶流太棒了! > 第422章 钳子落难记(第3页)
第422章 钳子落难记(第3页)
**程野**
字体古朴,似由树液自然凝结而成,与前五人风格一致,却又多了一丝粗粝的生命力,仿佛历经风沙跋涉而来。
玛拉莱最后一次来到树前,已是九十高龄。她无法站立,由孙子推着轮椅前行。她伸出手,轻轻抚过那三个字,嘴角扬起微笑。
当晚,她梦见自己变回二十岁,奔跑在初遇林昭的校园小径上。这一次,林昭没有回头,而是指向远方,说:
>“你看,他们都在听。”
她顺着方向望去,只见天地辽阔,万物生长。每一棵信树下,都站着一个普通人,他们或许平凡,或许沉默,但他们的眼睛清澈,耳朵敞开,心中盛满不属于自己的故事。
她醒来时,窗外晨曦初露。
三小时后,她在睡梦中安详离世。
葬礼很简单,遵照遗愿,她的骨灰撒入山谷溪流。速写本作为唯一遗物,交给了新一代记录者。最后一页写着:
>“真正的艺术,不是让人看见我想表达什么。”
>“而是让我看见你本来的样子。”
>“谢谢你们,让我活在一个肯听的世界。”
十年后的春分,“倾听日”首次实现全球同步静默。
那一刻,地球仿佛屏住了呼吸。
没有引擎轰鸣,没有电波传输,没有广告喧嚣。城市陷入温柔的寂静,人们牵手伫立,或抬头望天,或低头写字,或只是静静相拥。
而在南极科考站,研究员再次收到一封匿名邮件。
附件是一段音频,标题为《回家》。
他戴上耳机,听到的竟是十年前自己对着冰原喊出的那句:“如果有人听得见,请回答我。”
但这一次,回应来了。
先是轻轻一声铃响,接着是一个孩子的笑声,然后是一位老人用中文缓慢地说:“我在听。”
紧接着,千万种声音层层叠起??婴儿啼哭、恋人低语、工人号子、僧侣诵经、诗人朗诵、盲童唱歌……它们不分语言、国籍、时代,交织成一首无词的合唱,持续整整六十分零七秒。
音频结束时,屏幕上跳出一行字:
>“我们一直在。”
>“现在,轮到你了。”
研究员走出帐篷,抬头望向极光漫卷的夜空。
他知道,那不是大气放电。
那是世界在歌唱。
而在某条无人知晓的小巷尽头,一个年轻人蹲在地上,耐心听完流浪汉讲述三十年前错过的爱情。他没有给钱,也没有拍照,只是点头说:“谢谢你告诉我。”
起身离开时,他衣领内侧,一片叶形印记悄然浮现。
风拂过巷口,带来远处山谷的轻响。
仿佛有人在问:
>“下一个愿意倾听的人,会是谁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