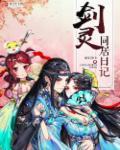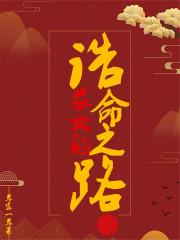笔趣阁>重启人生 > 0483拳头犯错游科吃饱(第3页)
0483拳头犯错游科吃饱(第3页)
风掠过山岗,吹动她的发丝,也吹动石碑前的花瓣。一只蝴蝶停在“李强”二字上,翅膀微微颤动,仿佛在聆听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,“声音邮局”的信箱越来越满。有人寄来烧焦的日记残页,附言:“火灾那天,我没能救出妹妹。这本日记是她唯一留下的东西。”;有人送来一对褪色的婴儿鞋,卡片上写着:“宝宝只活了三天。我们没来得及叫他名字。现在,我们叫他‘春天’。”;还有一个聋哑少年,用手语录像代替文字,志愿者逐帧翻译后写下:
>“我想告诉我死去的爸爸:
>我学会说话了。
>虽然声音很难听,老师说像石头滚下坡。
>可我每天练习,因为你说过,想听我叫你一声‘爸’。
>现在我能说了。
>爸。
>我在这里。”
许风吟把这些故事编入年度《回声录》,并在年末举办了一场无声朗读会。全场熄灯,大屏播放手语翻译影像,观众戴上耳机,听着志愿者同步诵读的文字。当那句“爸,我在这里”出现时,整个礼堂陷入一片压抑的啜泣。
年后,苏念正式成为“回声计划”的一线倾听员。她的第一个任务,是跟进一位因校园霸凌产生自残倾向的高中生。女孩不愿露面,只通过书信交流。苏念每次回信都不超过一百字,从不劝解,只是确认:“我收到了。”“我读完了。”“我在这里。”
三个月后,女孩寄来一封信,夹着一片干枯的樱花。
>“以前我觉得,痛苦是见不得人的东西,必须藏起来。
>可你每次都把它接过去,像接过一朵花。
>现在我知道,伤痕也可以被温柔对待。
>下周,我想见你一面。
>我想亲手给你一朵真的樱花。”
苏念回信只写了一句:“我会带茶来。我们慢慢说。”
四月将尽时,许风吟接到一个陌生电话。来电显示是甘肃某小镇,接通后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:
>“许老师,我是林小芸的学生,王建国。现在是村小校长了。
>上个月,我们组织孩子们写信给‘未来的自己’。有个小女孩写了:‘我想当老师,像林老师那样,照亮山路。’
>我们把所有信收起来,准备十年后拆封。
>可有个孩子问我:‘如果我活不到十年呢?’
>我不知道怎么答。
>后来我想起你们读过的那封信。我就告诉他:‘那就现在就说出来。只要有人听见,你就没有白活。’
>今天,我们全校朗读了林老师的信。
>孩子们都哭了。
>我也哭了。
>我想谢谢你们,让她的声音,一直没有断。”
许风吟挂掉电话,走到院子中央。春阳正好,樱花开至末梢,风一吹,花瓣如雨飘落。他伸手接住一片,轻轻夹进陈老师那本书的扉页??那本他曾反复翻阅、边缘已磨毛的《倾听的艺术》。
傍晚,他收到小满的新语音。背景是厨房的锅碗声,妈妈在哼歌,小满偷偷录下来。
>“许老师!妈妈今天做了糖炒栗子!她说,这是小芸姐姐最爱吃的。
>我们一起吃了,真的很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