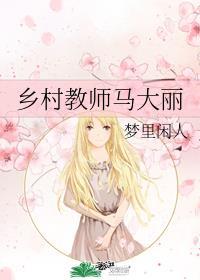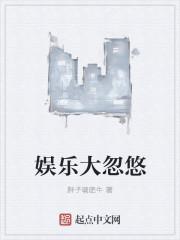笔趣阁>重启人生 > 0494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陈老祖(第3页)
0494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陈老祖(第3页)
“我在‘声音邮局’听过您的讲座录音。”年轻人摘下耳机,眼里泛起光,“去年冬天我差点辞职去打工,觉得活着没意思。后来听了您讲那个外卖员的故事……我就留下来了。现在我在自学心理咨询课程,打算明年报考社工证。”
许风吟愣住,随即笑了:“那这包糖送你。”
“不行不行!”年轻人急忙摇头,“这是我应该谢谢您才对。”
最后两人各退一步:许风吟买了两包,一包留下,一包带走。
回家路上,天边染上橘红。他想起多年前母亲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:“妈这辈子最遗憾的,就是没好好听你说说话。”那时他正忙着赶项目deadline,只敷衍地点了点头。直到多年后重读日记,才发现她曾在病床上写下:“我想抱抱他,可他总是匆匆来,匆匆走。”
如今,他每周都会去养老院做一次志愿倾听服务。老人们讲往事、抱怨子女、回忆青春,他只是安静听着,偶尔点头。有位失智老人总把他认成儿子,拉着他的手说:“你回来了,我就放心了。”他从不纠正,只轻轻应一声:“嗯,我回来了。”
第二天清晨,系统反馈:山东少女已接受面谈邀请,情绪初步稳定,愿尝试短期心理干预。她交给咨询师的第一样东西,是一张皱巴巴的打印纸??正是许风吟写给她的那封信。
与此同时,公众号发布一篇匿名投稿《致那位不曾谋面的回信人》:
>“我不知道你是谁,但我知道你一定也痛过。
>否则你不会懂得那种‘快要沉下去’的感觉。
>你也不会知道,一句‘我在’比一万句道理更有力量。
>昨晚我第一次对着镜子说了那句话:‘我不打算丢下你。’
>我哭了很久,但也睡了个久违的好觉。
>今天我要去上学了。
>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眼睛肿了,我就说:‘昨晚看了场感人的电影。’”
推文发布三小时,阅读量突破百万。评论区涌进无数相似的声音:“我也试了,说完那句话,好像心里真的松了点。”“我转发给了我妈,她回我:‘对不起,我一直以为你不缺爱。’”
许风吟没有转发,只是默默收藏。他知道,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轰轰烈烈,而是某个清晨,一个人愿意多吃一口早餐;是某个夜晚,一个人终于敢关灯睡觉而不必开着灯流泪。
一周后,“守护者行动”迎来首个成功案例:云南男孩的父亲在村干部和心理顾问多次沟通后,主动来到学校道歉。他在图书室外站了半小时,最终蹲下身子,对儿子说:“爸错了。以后你想说什么,我都听着。”
男孩没有立刻原谅他,但他接过父亲递来的雨伞??那是他第一次收到父亲买的礼物。
当晚,许风吟收到一封手写信,用铅笔一笔一划写在作业本纸上:
>“许老师:
>我爸昨天带我去吃了米线。他问我喜欢吃什么,我说加酸菜。他记住了。
>我把我们的对话写了下来,折成纸飞机,扔进了操场边的排水沟。
>我不知道它会不会飞出去,但我觉得,总会有个人捡到它吧?
>如果你看到了,请替我告诉那只飞机:
>它载着我和爸爸的新开始,一点都不重。”
他看完,眼眶发热。起身取出一张彩纸,折了一架更结实的纸飞机,在机翼内侧写下:“愿每一次起飞,都有归途。”然后放进信封,寄往云南。
夏日渐深,蝉鸣四起。“声音邮局”的用户数突破十八万。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自发组织“信件漂流”活动:把自己的信投入河流、塞进树洞、绑在气球上放飞。有人在河边捡到纸船,打开一看,里面写着:“如果你看到这封信,请告诉我,世界是不是还愿意听我说话?”便含泪回信,再沿原路寄回。
七月流火,许风吟受邀参加一场全国教育创新论坛。主办方安排他在闭幕式发言,题目定为《技术如何重塑情感连接》。他拒绝了预设讲稿,只带了一本笔记本走上台。
灯光聚焦之下,他翻开第一页,朗声读道:
>“1998年4月7日,星期二。
>今天我又躲在衣柜里哭了。
>我不明白为什么爸妈总吵架。
>我写了一张纸条放在餐桌上:‘你们能不能别吵了?我很害怕。’
>晚上回来,纸条不见了,饭桌上多了一盘我爱吃的红烧肉。
>可他们还是在吵。
>我把红烧肉倒进了垃圾桶。
>那是我第一次明白:有些话,即使说出口,也不会被真正听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