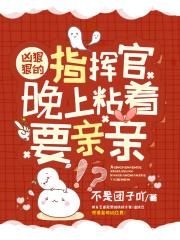笔趣阁>重启人生 > 0498陈老祖和他的公司(第1页)
0498陈老祖和他的公司(第1页)
清晨,鲁豫带着摄制组,来到北大科技园大厦楼下。
她要跟拍陈贵良一整天,做一期形式特别的专访节目。
陈贵良之所以答应鲁豫,而非跑去录制《对话》、《杨岚访谈录》,纯粹是因为目标受众不一样。
。。。
清晨的阳光斜斜地切过窗台,落在那行铅笔写下的字上,像一束微弱却执拗的光。许风吟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,指尖轻轻抚过纸船边缘,仿佛怕碰碎了某种正在成形的奇迹。他没有动它,就像当初没有动那只从内蒙古寄来的铁皮小船一样??有些东西,一旦被赋予意义,就再也不能轻率对待。
手机震动起来,是林晚发来的消息:“查到了。2003年12月17日,城南铁路桥下发现一名约十五岁的流浪少年,体温过低,意识模糊。送往市二院急救后转至市儿童福利院,登记姓名为‘陈默’,无亲属信息,次年被一对外地夫妇领养,去向不明。”
后面附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扫描件:瘦骨嶙峋的少年躺在病床上,盖着褪色的蓝格子被单,左手无意识地攥着一块干硬的面包皮。
许风吟的心猛地缩紧。
那块面包,是他那天早上省下来、塞进少年手里时说的:“先垫垫肚子,天总会亮。”
他记得自己当时还蹲下来,把围巾的一角拉高,遮住对方冻裂的脸颊,“你看,风再大,也吹不灭心里那点火苗。”
原来那个少年,真的存在过。
不是记忆错乱,不是中年臆想,而是真实发生过的、一次低头与一次伸手。
他闭上眼,喉咙发紧。二十年来,他无数次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帮到过谁,还是只是在空荡的山谷里自言自语。可此刻,这张照片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所有被尘封的信念。那个躲在桥洞下的男孩,不仅活了下来,还把那份微光种进了土地,长出了一座“纸船之家”。
他打开电脑,调出“回声档案”的总目录,在搜索栏输入“陈默”。系统跳出一条记录:三年前,一位匿名捐赠者通过基金会向“声音邮局”定向捐款五十万元,备注写着:“愿每个孩子都有地方躲雨。”捐赠人联系方式为空,但收款方确认该款项来自某建筑设计事务所项目分红账户。
许风吟顺着线索查下去,终于在一个建筑行业数据库里找到了关联信息??主设计师名叫陈砚,曾参与多个公益庇护空间设计,代表作《环形之舟》获亚洲青年建筑师奖提名。
而他的个人简介最后一句写道:“我一生都想建造一个不会让人蜷缩在角落的地方。”
许风吟笑了,眼角湿润。
他知道,就是他。
窗外,城市渐渐苏醒。公交车报站声、早餐摊油锅的滋响、学生背着书包跑过台阶的脚步声交织成一片。生活从来不是静止的展览,而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。而他们这些曾在岸边拾起纸船的人,早已不知不觉成了摆渡者。
当天下午,许风吟收到了青海“暖流计划”的最新进展报告。小女孩央金带着三个女孩在镇上租下一间旧茶馆,重新粉刷墙壁,挂上手绘菜单,每杯奶茶都附赠一张折纸教程卡片。最特别的是,她们设立了一个“沉默时间”??每天下午四点到四点半,店内熄灯,只留烛火,顾客可以写下心事投入墙角的木盒,每周由团队整理后寄往“声音邮局”。
报告末尾附了一段录音转文字:
>“许老师,今天有个阿姨哭了好久。她说她儿子去年车祸走了,她一直不敢回家,怕看见空房间。我们给她泡了姜汁红糖奶,她走的时候留下一封信,说这是两年来第一次觉得有人‘听懂’了她的痛。我想,也许我们做的不只是奶茶,是在给心冷的人一点点热气吧。”
许风吟将这段话复制进年度白皮书第一章,标题命名为:《热气的力量》。
与此同时,“纸船护航计划”第二批受助名单出炉。其中有一个叫周涛的十六岁少年,住在甘肃陇南山区,患有重度社交恐惧症,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几乎未开口说话。母亲早逝,父亲常年在外打工,他独自住在半塌的老屋里,靠捡废品维持生计。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方式,是每月一次去镇上亲戚家借网,在“声音邮局”公众号留言区留下极短的话:
>“我还活着。”
>“今天下了雨,屋顶漏得厉害。”
>“我想上学。”
志愿者团队实地走访后拍回视频:屋内昏暗潮湿,墙上贴满他自己画的纸船图案,每一艘都标着日期和一句话。最近一幅写着:“如果我能走出去,我要当一名造船的人。”
许风吟当即决定亲自前往。临行前夜,他在办公室整理资料,忽然听见门外有动静。推门一看,林晚抱着一摞手工信封站在走廊尽头,身后跟着几位志愿者,每人手里都提着装满彩纸、蜡笔、录音机的小箱子。
“我们一起去。”林晚说,“这次不止是你一个人的声音。”
一路颠簸七小时,翻越两座山梁,车停在村口时已是黄昏。炊烟袅袅升起,几个孩子围在井边打水,见到陌生人纷纷躲闪。唯有周涛站在自家院门口,远远望着,身体微微发抖,眼神却透着一种近乎倔强的清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