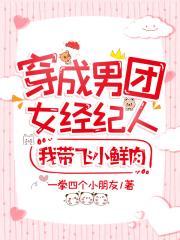笔趣阁>虎贲郎 > 第734章 后知后觉(第1页)
第734章 后知后觉(第1页)
金城,自夏阳郡撤兵的赵云所部就在金城外的黄河两岸休整、游牧。
河中地区被命名为夏阳郡后……也只是被命名为夏阳郡。
这里人口要么从叛被强迁,留下的良善民众委实不多。
休说供养一郡,就是。。。
春风拂过晋阳城外的信义田,麦苗初齐,绿浪翻涌。赵明远拄着一根竹杖,沿田埂缓行,脚边泥土松软,沁出湿气。他已不再佩剑,也不再穿铠甲,只一身粗布短褐,袖口磨得发白。身后跟着几名年轻监察生,手中捧着账册与算筹,正低声核对春播面积。
忽然,前方传来喧闹声。一群农夫围在田头,指指点点,神色愤然。一名老妇跪在泥地里,抱着一捆被踩烂的秧苗痛哭:“那是我家三亩口粮田!昨夜官渠放水,竟把堤坝全开了,水冲下来,苗都毁了!”
赵明远皱眉走近,问明原委。原来县府为灌溉豪族私田,擅自更改水道,将主渠引向北坡,又未提前示警,致下游十余户百姓田地遭淹。更有甚者,管水吏还扬言:“种田人不懂大局,少抱怨。”
“这就是‘民为邦本’?”一名监察生怒道,“他们连《宪章》第三条都不认了!”
赵明远蹲下身,从泥中拾起一片残叶,轻轻抖落泥浆。良久,他起身,声音不高,却字字清晰:“去请水署主簿来此,带上去年分水图录和今年调度令。若不来,我们就去县衙门口讲学。”
半个时辰后,主簿匆匆赶到,脸色阴沉。他瞥了一眼赵明远,冷声道:“赵先生如今不过一介布衣,何须插手公务?此事自有上峰定夺。”
“我不是以身份说话。”赵明远平静道,“我是以《宪章》说话。你我皆是大汉子民,谁都有权质问:为何公器私用?为何百姓蒙损?”
主簿冷笑:“你莫要煽动民意。这水渠本就归县令统筹,你说的话,算什么法?”
话音未落,人群中走出一个瘦小少年,正是那日画狼牙坠的孩子。他举起手中一本薄册,大声念道:“《信义塾律解?卷二》第七条:凡因官吏擅改水利而致民田受损者,无论品级,皆应赔偿并罢职查办!此条依《宪章》第九、第十款推演而来,已在十二郡通行!”
众人哗然。主簿惊愕地看着这孩子,又看向赵明远:“你竟教孩童干预政事?”
“他们不是干预政事。”赵明远扶住孩子的肩,“他们在学习如何不做顺民。你们可以关掉他们的嘴,但关不掉他们的眼睛。他们会看,会记,会一代代传下去。”
此时,远处尘烟骤起,数十骑快马疾驰而来,为首者披黑袍,佩铜符,乃是朝廷巡查御史。围观百姓纷纷退避,唯独赵明远不动。御史勒马停步,目光扫过现场,沉声问:“何事聚众喧哗?”
监察生上前呈上证据:被毁田亩图、水流痕迹比对、村民联名状、以及主簿昨夜出入豪族宅邸的目击记录。御史翻阅片刻,面色渐凝。他跳下马,亲自踏勘田地,又命随从测量水位落差,最终转身喝令:“即刻恢复原渠,赔偿损失,并将主簿收押,待查实后奏报朝廷!”
人群爆发出欢呼。主簿面如死灰,被当场带走。那老妇扑通跪下,朝赵明远磕头:“青天啊……真有您这样的人活着,我们穷骨头才敢抬头喘气。”
赵明远扶她起身,摇头:“我不是青天。我只是个守约的人。当年阿兰朵南下送信,不是为了让我们跪着活,而是为了让我们站着说话。”
当晚,信义塾灯火通明。百余名监察生齐聚堂前,复盘此案。赵明远立于案前,提笔在墙上挂起的新地图上划出一条红线:“记住,权力最怕什么?不是对抗,不是暴动,而是记录。每一笔贪墨,每一次毁约,只要被写下来、算清楚、传出去,它就再也无法假装不存在。”
他顿了顿,环视众学子:“从明日开始,我们要做一件从未做过的事??建立‘信义档案库’。所有揭发案件,无论大小,全部归档编号,公开查阅。每三年发布一次《天下失信录》,列出十大失信官吏、十大失信机构、十大失信政策。我们要让‘失信’二字,成为比死更可怕的惩罚。”
有人迟疑:“可若是朝廷压下不报呢?”
“那就我们自己报。”赵明远淡淡道,“报纸可以禁,书可以焚,但人心不会瞎。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真相,火种就不会灭。”
话音刚落,门外传来急促脚步。一名风尘仆仆的监察生冲入,双手奉上一封泥封文书:“先生!北方急报!赫连曜率部南迁三百里,在阴山南麓建‘信义营’,开垦荒地两千顷!他还派人送来一封信。”
赵明远接过信,拆开细读。信纸粗糙,墨迹斑驳,却是赫连曜亲笔所书:
>“赵兄:
>草原旱情未解,贵族仍囤粮自肥。我率三千部众南徙,非为投靠,亦非乞食,只为践行当日之诺??种下你给的种子。
>如今麦已破土,百姓称其为‘南中信’。他们说,这是用信换来的粮食。
>昨夜有长老劝我趁势南下,夺城占地。我说:若我们只为利而来,阿兰朵的血便白流了。
>我只求一事:请派十名农师北上,教我们轮作与蓄水之法。
>若允,请在城头升起双纹旗。”
赵明远看完,久久无言。良久,他走到院中,亲手升起一面旗帜??狼牙坠与稻穗交织,底色为白。翌日清晨,北方哨站回报:信义营方向升起同样旗帜,三起三伏,似在致礼。
三日后,十名精通水利与耕作的监察生启程北上,每人背负一袋晋阳良种、一套《农政全书》抄本,还有一枚木制狼牙坠作为凭证。临行前,赵明远叮嘱:“你们不是去施恩,是去学习。真正的信义,不在纸上,而在泥土里,在人心里。”
然而,风暴并未止息。
清明时节,京师传来消息:皇帝病重,太子监国。一道密旨悄然下达,命各地官府严查“民间结社”,尤其针对信义塾及其监察生网络。数郡响应,突袭搜查地方学堂,拘捕学生十余人,罪名竟是“伪造文书、诽谤官长”。
赵明远闻讯,立即召集骨干商议。林照儿连夜赶至,鬓角微霜,眼中却仍有锐光。“这不是普通的打压。”她分析道,“是有人想借皇权交替之际,一举铲除异己。他们知道,只要你还在,门阀就永远无法回到从前。”
“那就让他们看看。”赵明远站起身,“什么叫‘越压越亮’。”
他当夜修书五封,分别致太学祭酒、边郡刺史、商会长老、军中旧部及赫连曜。信中不诉冤屈,只列事实:历年监察成果、百姓受益数据、失信官员名单,并附一句:“若今日沉默,则明日人人皆可被无声抹去。”
同时,他下令启动“千灯计划”??凡受过信义塾帮助的村庄,每村在月圆之夜点亮一盏灯笼,写下本地见证的失信之事,悬于村口,供路人阅览。短短半月,百余村落响应,夜空中星火点点,宛如银河落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