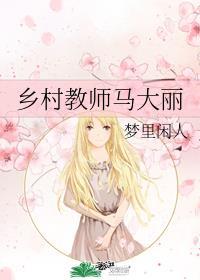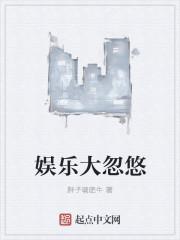笔趣阁>虎贲郎 > 第738章 反复拉扯(第2页)
第738章 反复拉扯(第2页)
她是陈九章之女,名唤陈知微。三年前地窖塌方,她趁乱逃出,靠记忆中的地图穿越荒漠,途中救下一队被官军追杀的西域商人,得知龟兹王已秘密成立“信义盟会”,便一路西行,最终在南山聚拢流亡志士,建寨讲学,收容因言获罪者,传授《宪章》与《法理纲要》。
“我不敢用真名。”她将册子递给赵明远,“但我把你们写的每一句话,都补上了注解、案例、判例。我还写了新的章节??《监察之道》《民议之制》《跨境平冤法》。若这些也算信义之书,请让它继续活下去。”
赵明远翻开书页,指尖颤抖。那些字,一笔一划,皆如刀刻石,充满愤怒与希望交织的力量。他在第一页写下批语:“此书非续,乃新生。作者非一人,乃千万无名者之心血。”
当夜,守心寨燃起篝火,全寨上下齐聚广场。赵明远站在石台上,手持《信义续编》,宣读新章第一条:“凡因言获罪者,无论时代远近,皆应予以平反。其名誉须恢复,其后代应受教养之助,其事迹当载入国史。”
话音落下,全场寂静。片刻后,一位白发老者拄拐而出,跪地痛哭:“我儿因抄录《南中信义录》被斩于市,头颅悬挂三日……今日,我终于听见公道二字!”
接着,第二人、第三人相继跪下,有人抱着残卷,有人捧着骨灰坛,有人只是默默举起双手??那是曾经戴过镣铐的手。五百余人,齐声呼喊:“我们要信义!我们要真相!”
声音穿透山谷,惊起群鸟,飞向远方。
七日后,赵明远命人将《信义续编》全文誊抄九份,分别送往洛阳、长安、敦煌、辽东、交趾、成都、建康、龟兹、平城。每一份皆附亲笔信一封,末尾皆书同一句话:“火可熄,风可止,人心不可囚。信义既起,山河必变。”
返程途中,他们在一处驿站接到急报:长安特别法庭已开审贞观十七年旧案,首名被告竟是现任吏部尚书崔衡??崔胤之孙。庭审当日,陈知微亲自出庭作证,出示当年从西京别苑带出的半块腰牌,以及一份由三名幸存狱卒联署的供词,证明阿兰朵确曾被秘密关押,且梁承业曾试图营救。
更令人震动的是,一名年逾八旬的老宦官当庭自首,自称曾奉张让之命参与伪造“梁承业自焚”现场,实则将其活埋三日,后因良心难安,偷偷通风,助其短暂逃脱,终未能救。
“他最后对我说:‘告诉世人,我不是叛贼,我是想让草原的孩子也能读《论语》的人。’”老宦官伏地嚎啕,“我瞒了三十年,今晚若不说,死后必堕无间地狱!”
舆论哗然。崔衡当庭昏厥,数日后上书请辞,称“家族蒙羞,无颜居庙堂”。皇帝迫于压力,准其致仕,并下令追夺崔胤生前一切封赠,拆毁祠堂。同时,正式下诏追封梁承业为“忠信太子”,谥曰“昭”,命礼部择日举行国葬。
然而,风暴并未平息。
四月初八,佛诞日。长安西市再度起火,但这回收焚的不是黄麻布,而是一整箱朝廷邸报。纵火者是一名年轻学子,被捕时高呼:“你们刊登的全是谎言!梁承业不是逆子,他是先知!”随即咬舌自尽,血书遗言留在袖中:“信不死,人在!”
与此同时,北方边境传来警讯:赫连曜虽未称王,但已联合鲜卑、乌桓、敕勒等十二部落,组建“信义联军”,宣布若朝廷拒不交出全部档案、不惩办所有涉案权贵,将于秋收后举行“大巡行”??即率十万骑兵南下,直达潼关,要求面圣陈情。
朝廷震恐。御前会议上,有大臣主张武力镇压,称“此乃胁君之举,断不可纵”;亦有重臣悄然提议和解,认为“民心已失,兵不可恃”。最终,皇帝召见赵明远弟子百人团代表,询问条件。
代表答:“无需金银,不要官职。唯求三事:一、公开全部辛亥三号与癸卯零号档案;二、设立独立平冤院,由民间推选五人与朝廷共审积案;三、废除‘以言定罪’律条,颁布《言论自由法》。”
皇帝沉默良久,终允前两项,第三项暂缓。
五月端阳,特别法庭公布首批调查结果:贞观十七年事件系由崔胤、张让等人策划的政治构陷,旨在阻止胡汉和议,维护战争利益集团。阿兰朵被正式宣告无罪,赵明远恢复一切功名与待遇,追赠银帛,然二人皆拒不受赏。
赵明远回书道:“我所求者,非个人荣辱,乃制度清明。若朝廷真悔过,请将《晋阳宣言》列入科举策问,让天下学子皆知何为信义。”
六月盛夏,太学改制启动。《信义录》正式纳入“明经科”考试范围,与《春秋》《礼记》并列。更有惊人之举:新设“信义策论”专场,考生需就“如何建立独立监察机构”“如何保障异见者权利”等题展开论述。试题一经公布,洛阳纸贵,民间争相传抄。
而在晋阳,信义塾扩建为“信义书院”,设法学、史学、伦理学三科,招收胡汉子弟,不分贵贱。阿兰朵亲授“女性与信义”课程,讲述历代被抹去的女子志士,包括她母亲??那位在草原上第一个用汉字记录牧歌的女祭司。
赫连曜则在北方推行“村议制”,每百户推选一人进入民议庭,决定赋税、徭役、边贸等事务。他更下令拆除旧时长城残段,取其砖石修建学堂与医馆,碑文刻曰:“此墙曾分胡汉,今化育新人。”
秋分再至,赵明远再次登上思子台。这一次,他不再独奏。阿兰朵抱琴而来,赫连曜击节为拍,林照儿执笔记录,五百学子列队于田埂,齐声吟唱新编《信义颂》:
>“昔有囚者,幽于九渊;
>今有书声,响彻山川。
>一笛一琴一玉坠,
>换得乾坤正气还。”
曲毕,赵明远举起竹笛,面向西方落日,轻轻吹响最初的旋律??那个曾寄托思念与绝望的调子。但这一次,笛声不再断裂,不再呜咽,而是平稳悠长,如同大地呼吸,如同历史转身。
他知道,这场持续十五年的黑夜,终于迎来了第一缕不可阻挡的晨光。
多年后,当《信义法典》成为帝国新律的基础,当“信义院”取代御史台成为最高监察机关,当胡汉通婚不再需要特旨批准,人们已很少提起那些名字。但每逢春分,晋阳百姓仍会自发聚集信义田,点燃灯笼,摆放竹笛、胡琴与玉坠,纪念那段没有刀光却胜过千军万马的岁月。
而那两株松柏,早已亭亭如盖,枝叶相触,根脉相连,仿佛在无声诉说:最深的信义,从来不是来自权力的恩赐,而是源于平凡之人,在黑暗中不肯放手的坚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