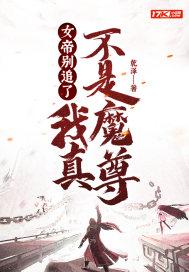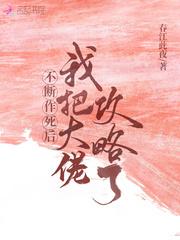笔趣阁>我的哥哥是高欢 > 第277章 演戏自然就要演全套(第1页)
第277章 演戏自然就要演全套(第1页)
众人皆错愕的抬头看向侯莫陈悦,高羽亲率十万大军前来攻城。
便是尔朱荣本人在此听到这消息都会忍不住的皱眉。
那可是高羽啊!
当世‘项羽’,号称勇武可以比肩古之霸王,犹如霸王复生的男人!。。。
春去秋来,归仁堡的麦田泛起金浪。高澄每日清晨便拄着一根榆木拐杖,沿着田埂缓步巡查。他的腿伤从未痊愈,每逢阴雨便钻心地疼,可他从不抱怨。风吹日晒已将他昔日白皙的脸庞刻成古铜色,眉间沟壑深如刀凿,唯有那双眼睛,愈发清明。
这一日,天光微明,露水未干。几个牧童赶着羊群路过麦田,见一人蹲在地头,正用枯枝在地上画图讲解:“冬小麦须深播浅覆,根扎得深,才扛得住北风。”孩子们围拢过来,听得出神。一个瘦小的女孩怯生生问:“先生,你是不是从前那个……太子?”
高澄抬起头,笑了笑,眼角皱纹舒展:“我曾是,但那身份早已烧成了灰。现在我只是个教人种地、识字、讲理的先生。”
女孩眨眨眼:“那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?我们是铁勒人,你们汉人不是说我们是野蛮人吗?”
高澄沉默片刻,起身走到田边,拾起一穗沉甸甸的麦粒,轻轻吹去浮尘,递给她:“你看,这麦子是从西域传来的,最早也不生在中原。可如今它养活了千千万万人。人心亦如此??不分胡汉,谁能带来粮食与安宁,谁就是亲人。”
女孩接过麦穗,紧紧攥在手心,仿佛握住了某种承诺。
归仁堡的学堂里,书声琅琅。十二名学生齐声诵读《新律?民权篇》:“凡属编户,皆为齐民;有罪止其身,不得连坐;官吏欺压百姓者,重惩不贷。”声音穿透土墙,在草原上飘得很远。
校长阿史那达干站在窗前,望着远处那个佝偻却坚定的身影,低声对身旁助手说:“他来了不过一年半,可这里变了。以前孩子不敢上学,怕被征兵;女人不能说话,怕遭鞭打。如今他们敢写诉状,敢当众质问屯田官为何克扣口粮。这不是政令强推的结果,是他一点一滴教出来的。”
助手叹道:“可朝廷真能容他长久在此?毕竟他曾执掌东宫,权倾朝野,杀戮无数……”
“所以他不敢停。”阿史那达干望着高澄走进教室的身影,“他知道,只要停下一天,过去的血债就会重新涌上心头。”
当天午后,驿马疾驰而至,送来一封加盖御印的公文。高澄拆开一看,竟是晋阳诏令:因《北行录》震动朝野,“高澄十二策”全面推行,全国清查私役、伪籍、滥征三弊,已有七十三名官员落职查办,其中三人斩首示众。诏末附高洋亲笔批语:“昔以威立国,今以信立邦。尔之所述,乃万民之喉舌,非逆臣之哀鸣。”
高澄读罢,久久伫立院中。夕阳洒在他肩头,影子拉得很长,像一道横贯岁月的裂痕。他忽然转身回屋,取出一只粗陶碗,盛满清水,置于案上。然后跪下,对着水中倒影深深叩首三次。
夜深人静,他在灯下提笔续写《北行录》第十三卷??本不在原计划之内,但他觉得还有话要说。
>“臣尝以为,治国在于权谋,驭民贵在震慑。故少年得志时,设密探、行株连、焚书院、囚言官,自谓‘铁腕定乾坤’。然今日行走千里,目睹妇人抱尸哭于荒冢,孩童拾骨充饥于废村,方知暴政之下,无一人得安。
>
>有老妪居雁门山麓,三子皆因‘通匪’罪名处决,实则只为偷挖半筐野菜。彼时我批阅奏章,仅一句‘依律处置’四字了事。今见其人独守破屋,日日摆三副碗筷,唤儿归食,声嘶力竭,无人应答。我竟无颜直视其目。
>
>民不畏死,奈何以死惧之?此非老子空谈,乃血写箴言。
>
>臣愿终老于此,非求赦免,惟望以余生补寸功于万一。若有一人因我之言而免冤狱,有一家因我所授耕技而不饿死,则吾心稍慰。”
墨迹未干,窗外忽传来脚步声。一名巡田御史模样的青年官员推门而入,拱手道:“高先生,我是奉命巡视北境的第六批寒门学子,途经此地,特来拜谒。读过《北行录》,夜不能寐。请问先生??如何才能不让新政沦为新弊?”
高澄吹熄油灯,点燃一支松脂火把,火焰跳跃映照着他苍老的面容。
“你可知归仁堡最初建城时,用了多少块夯土?”他问。
青年摇头。
“三千六百八十九块。每一块,都是百姓亲手筑成。官府本欲派役夫强征劳力,是我拦下,改以工代赈:一家出力一日,记一分,积满十分可换一斗米、一本《识字启蒙》。结果人人争先,连八十老翁也来搬石。”
他顿了顿,声音低沉:“制度若离民心,纵有千条法令,不过纸枷锁。而一旦百姓觉得自己是在为自己筑城,哪怕风吹雪打,墙也不会倒。”
青年怔住,良久才道:“所以您教的不只是法律和农事,更是让他们相信??这天下,也有他们的一份。”
“正是。”高澄点头,“否则,公平只是强者施舍的残羹,而非众人共守的契约。”
次日清晨,高澄带着几名学生前往边境勘测水渠路线。途中经过一片乱葬岗,枯骨遍地,碑石倾颓。一名小女孩正在给一座小坟堆插花,见他们到来,怯怯退后。
高澄走近细看,墓碑上刻着:“铁勒孤儿阿塔尔之墓,年七岁,殁于饥寒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