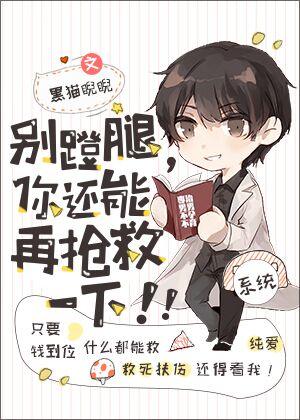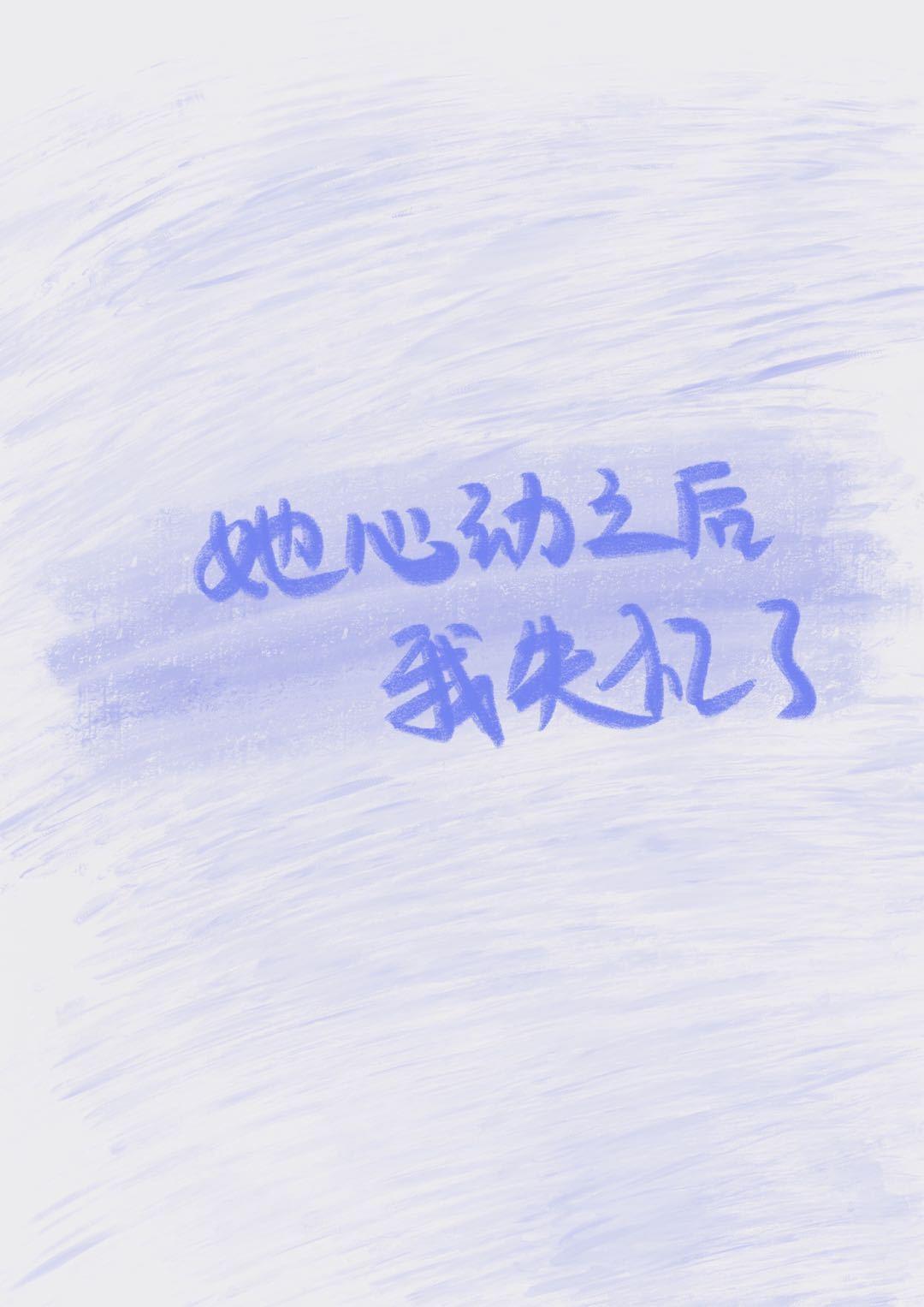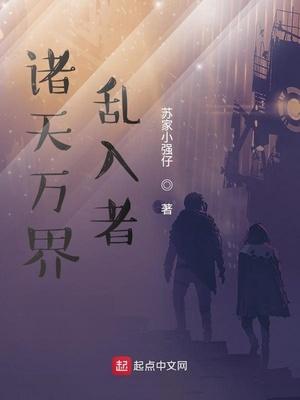笔趣阁>世子稳重点 > 第一千零三十七章 民间秩序(第1页)
第一千零三十七章 民间秩序(第1页)
“早上的第一泡尿”,纨绔们当得起这个比喻。
其实赵孝骞自己也是纨绔出身,当年刚穿越过来时,还谋划过著名的马场格勒伏击战,把曾经设计欺负过自己前身的纨绔们狠狠揍了个遍。
而赵孝骞也因那一战封。。。
车队在昆仑山的余脉中穿行,风雪渐歇,天光却未放晴。云层低垂如铁幕,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沈知意坐在车窗边,指尖轻轻摩挲着那张少年写下的纸条,背面她添上的字迹已被体温烘得微温。“那就让我们一起,做个还在路上的人。”这句话像是一颗埋进冻土的种子,尚不知能否发芽,却已悄然裂开壳缝。
灰隼从后座醒来,脸色苍白,眼底浮着一层深不见底的疲惫。他盯着平板屏幕,数据流依旧汹涌,但内容变了??不再是情绪指数的狂飙,而是全球范围内自发涌现的“真言录音”。人们开始上传自己最原始、未经修饰的话语:有母亲对孩子说“我其实讨厌你哭”,也有士兵对着亡友的照片喃喃“我不配活着回来”。这些声音杂乱、破碎、刺耳,甚至令人不适,可它们真实得让人心颤。
“系统没有崩溃。”他低声说,“它在进化。认知稳定协议被否决了,七国联席会议最终投票结果是13比12。差一票。”
“那一票是谁?”沈知意问。
“中国代表。”灰隼抬头看她,“是你父亲。”
车内一片寂静。沈知意怔住,手指僵在纸条边缘。她知道父亲是国务院特别顾问,也知道他在高层影响力极重,但她从未想过,他会在这个节骨眼上,站在她这一边。
“他投了反对票?”她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
“不只是反对封锁网络。”灰隼递过一份加密文件,“他还公开提交了一份《命名权归还提案》,主张废除国家主导的身份标签体系,允许公民自主申报社会称谓,并设立‘沉默期’制度??每个人每年可申请七日‘无名状态’,在此期间不接受任何身份调用,也不承担相应义务。”
沈知意闭上眼,眼前浮现出那个总穿灰呢大衣、说话严谨到近乎刻板的男人。小时候,他教她背《论语》:“名不正,则言不顺。”如今,他自己却亲手推翻了这句话的根基。
“他为什么要这么做?”少年靠在椅背上,声音沙哑。
“因为他看了你的视频。”灰隼说,“不止是你,还有王老师抱住逃犯的那一幕。他说,那是三十年来,第一次看到‘人’而不是‘角色’在行动。”
沈知意睁开眼,喉咙发紧。她忽然明白,父亲不是转变了立场,而是在那一刻,终于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声音??就像他们在“无名堂”所做的那样。
车队驶出峡谷,进入一片荒原。远处的地平线上,一道孤零零的铁塔耸立,锈迹斑斑,顶端挂着一面破旧的风铃,在寒风中发出断续的叮当声。玉简突然震动,悬浮而起,投影出一段模糊的地图:一条蜿蜒的线路指向西北,终点标注着两个古字??“信墟”。
“第七井不在城市,也不在庙宇。”少年凝视着影像,“它在遗忘之地。”
“什么是遗忘之地?”特勤队员问。
“是那些被时代甩下的人待的地方。”沈知意轻声说,“养老院、废弃矿区、边境哨所、精神病院……所有不再被需要的记忆,都会流向那里。”
灰隼调出卫星图像,放大那片区域。铁塔周围散布着十几座低矮建筑,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集体宿舍。热成像显示仍有生命体征活动,但信号极其微弱,仿佛一群游魂在苟延残喘。
“这里曾是‘国家记忆备份中心’。”灰隼翻阅档案,“冷战时期,政府担心核打击导致文明断层,于是建立了一批地下资料库,收录所有重要文献、口述史、科学数据。后来技术进步,云端存储取代了实体档案,这些地方就被遗弃了。可有些人没走。”
“守档人。”少年说,“他们自愿留下,守护那些没人再看的记录。”
车队缓缓靠近铁塔。风铃声越来越清晰,每一声都像是某种召唤。大门早已锈死,特勤组用液压钳破开一道缝隙。屋内昏暗潮湿,空气中弥漫着纸张霉变的气息。一排排铁架延伸至黑暗深处,堆满泛黄的手稿、磁带、胶片盒,许多封皮上写着“绝密”或“永久封存”。
中央大厅有一台老式放映机,仍在运转。银幕上跳动着黑白画面:一位老人坐在桌前,面对镜头,神情平静。
>“我是第十七任守档人,林昭。今日为公元2049年3月17日。本中心剩余电力预计维持七十二小时。若无人接替,我将执行最终程序:点燃全部纸质档案,确保信息不落入错误之手。这不是毁灭,是守护。有些真相,必须有人记得;也有些记忆,必须有人选择不传播。”
画面戛然而止。
“他已经死了。”一名队员检查控制台,“氧气耗尽,三个月前。”
沈知意蹲下身,翻开脚边一本登记簿。最后一页写着:
>“今日有人来访。年轻女子,穿蓝布衫,提竹篮。她说她是邻村小学老师,想查一份1962年的学生名册。我问她查谁,她说:‘一个叫李文秀的孩子。’
>我告诉她,那份档案早在七九年就销毁了。
>她笑了,说:‘我知道。我只是想知道,是否真的有人记得她存在过。’
>我们聊了很久。她走时,送了我一朵野花。
>这是我三十年来看到的第一朵花。”
沈知意的眼眶红了。
“她不是为了查档案去的。”少年站到她身边,“她是去确认‘相信’这件事本身还有意义。”
就在这时,玉简再次震动,投射出新的文字:
>“第七环试炼:信之所立,不在证据,而在愿信本身。欲知真理,先承无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