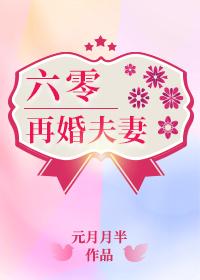笔趣阁>秦人的悠闲生活 > 第三百二十四章 张良的信念(第2页)
第三百二十四章 张良的信念(第2页)
回到张掖不久,朝廷又有新令:鉴于护羌校尉辖区日益扩大,事务繁杂,特增设“西域都护府”雏形机构,暂由刘肥兼领,统辖河西以西至鄯善一线军政事务,有权调度边军、审理胡汉纠纷、批准商队通行。
诏书送达当日,刘肥独自登上城北高山,遥望西方无垠大漠。夕阳如血,洒落在祁连雪峰之上,映出一片金红。他忽然想起八年前初入军旅时,灌婴曾问他:“你为何从军?”
那时他答:“为建功立业,扬名天下。”
如今他想,答案早已不同。
傍晚归营,案头已堆满文书:有屯田户申请扩建水渠的呈文,有商队遭遇沙暴损失货物的索赔状,还有车师国新任国王派来的谢罪使节名单??原来前番袭击秦军的贵族已被族人诛杀,新君上位后立即遣使请罪,愿年年进贡,岁岁称臣。
刘肥提笔批阅,字迹工整有力:“准其所请。然须立誓碑于国境,刻写‘永奉大秦正朔’六字,并派子弟入敦煌译学馆读书十年,方可视为诚信。”
处理完政务,他唤来亲兵,取出一封密信,命其快马送往咸阳。信中写道:
>“臣刘肥顿首再拜,谨奏陛下:
>臣自受命西戍,迄今六载。亲见荒原变绿洲,胡俗渐染华风。今乌孙归附,车师请罪,丝路安宁,百姓乐业。此非一人之功,实赖陛下深谋远略,群臣协力经营。
>然臣窃以为,治西域之道,贵在柔远能迩,恩威并施。徒恃兵甲,则人心不服;专务怀柔,则边境生患。唯以制度立信,以教化润物,方能使异族自化,疆土永固。
>臣虽愚钝,愿毕生效力于此。纵死沙场,亦无憾矣。
>唯望长安春色,勿忘塞外风霜。”
信使出发后,刘肥走出营帐,仰望星空。北斗七星清晰可见,斗柄正指向西北??那是匈奴故地的方向。
他知道,风暴尚未过去。蒙恬的大军已在酒泉集结,随时准备出击。而他自己,也将迎来更严峻的考验。
然而他不再焦躁,也不再急于求战。因为他终于明白,真正的胜利,不在一时胜负,而在岁月沉淀之后,是否仍有人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,是否仍有孩童朗朗诵读《秦律》,是否仍有老人捧起黑土热泪盈眶。
这才是秦人的悠闲生活??不是无所事事,而是心中有定;不是逃避纷争,而是从容布局;不是贪图享乐,而是坚信未来。
数日后,第一批由咸阳派出的“西域学宫”博士抵达敦煌。他们带着成箱的竹简、铜尺、医书、农具模型,还有整整一辆车的桑苗??准备在这里推广养蚕缫丝。
孩子们围在城门口,好奇地看着这些穿着儒袍的先生们。有个小女孩怯生生地问:“老师,我们可以学写字吗?”
为首的博士蹲下身,温和地说:“当然可以。从明天开始,你们就能学到‘人’字的第一笔。”
与此同时,在遥远的咸阳章台宫,皇帝再次展开那幅巨大的西域舆图。他拿起朱笔,在敦煌以西轻轻一点,写下两个字:“轮台”。
萧何站在一旁,轻声道:“陛下已有十年未曾亲征,可天下却比从前更加辽阔。”
皇帝笑了笑:“朕老了,脚步走不远了。但有人替朕走下去。刘肥、曹参、蒙恬……还有那些还不知名的小吏、农夫、士兵。他们才是帝国真正的脊梁。”
窗外,春风正暖,吹开了宫墙内的桃李。花瓣飘落案头,盖住了“轮台”二字,却又仿佛为其加冕。
而在敦煌城外,第一茬麦苗破土而出,嫩绿如烟,铺展在广袤的大地上,像是无声的誓言,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。
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有多少风雨,但所有人都相信,只要这条路继续走下去,终有一天,从东海之滨到葱岭以西,所有的河流都会流向同一个方向??那是秦律所至之地,是王化所及之乡,是无数普通人用双手与信念筑起的,永不倾塌的江山。
刘肥骑马巡视边境归来,路过一处新开垦的村落。几个孩子正在村口练习写字,用树枝在地上划出歪歪扭扭的“秦”字。他停下马来,静静看了一会儿,然后翻身下马,蹲在孩子们身边,一笔一画地教他们如何写出最后一捺。
“这一笔要稳,要长,就像咱们走过的路一样。”他说。
孩子们认真模仿,笑声在春风中飞扬。
远处,夕阳缓缓沉入戈壁尽头,余晖照亮了新立的界碑??上面刻着四个大字:**大秦西境**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