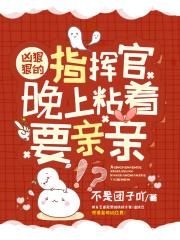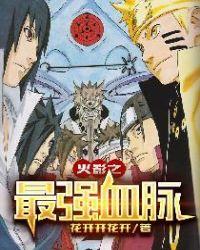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剑宗外门 > 第373章 丹散(第1页)
第373章 丹散(第1页)
这镇岳,乃是张承的本命法宝,九柄一套。
此刻,许是感受到了他的死志,这辉光无比强烈。
九道金色的剑影,再次合为一道,不要命似的地斩击着血色长戈与护体魔气。
这可以说是金丹修士最后的底。。。
雪落无声,却压不住人心深处的躁动。李念伫立碑顶良久,残玉贴于信纸的那一瞬,仿佛有股温热自指尖蔓延至心口,像是血脉在回应血脉,历史在呼唤历史。她没有流泪,只是将密信连同那半块玉佩一并收入怀中,动作轻缓,如同安放一个沉睡多年的梦。
她缓缓走下照心碑,青石阶上积雪未化,每一步都留下清晰足迹。风从北面吹来,带着刺骨寒意,也带来了远方的消息??朝廷虽已封禁忆馆,可民间反扑之势如春雷暗涌。南方三州百姓自发集资重印《补遗录》,以“家训”之名藏于族谱夹层;西北商旅则将《贞元实录》拆分为数十段商路记账文书,混入货单之中,一路西行,直抵龟兹、疏勒。
更令人震动的是,京畿十三道关卡中,竟有五处守吏暗中放行违禁书卷。一名小吏被捕后当堂朗读《南宫萤奏对录》,声泪俱下:“我母早亡,父为县学教谕,临终前犹念‘史不可欺’四字。今我纵死,亦不愿子孙活在谎言之下!”
朝堂震动,御史大夫请斩此人以儆效尤,然刑部尚书却悄然递上一份名录:那五名放行书卷的守吏,竟皆出身寒门,少年时曾在地方书院受过南宫萤所倡“义学”之惠。此事被有心人挖出后,舆论哗然。街头说书人编了一出新戏《五吏焚书夜》,唱词中有句:“你烧的是纸,我护的是根。”
李念回到无名堂时,十一使已齐聚密室。火盆中炭火烧得正旺,映得众人面色通红。她取出商船主的密信,一字一句读完,室内寂静如渊。
片刻后,刻工老周颤声道:“李姑娘,这玉佩合了,是不是……咱们就能对外宣示李家血脉未绝?”
“不能。”李念摇头,“李昭身在扶桑,若此时公开身份,非但救不了中原之局,反而会引来朝廷追索海外遗孤,牵连无辜。更重要的是??”她目光扫过众人,“我们早已不再需要一个‘正统后人’来证明真实的存在。真实本身,已是千千万万人的选择。”
班主阿娥点头:“说得是。如今《照心碑下血犹温》已在二十城连演百场,有人看完当场跪地发誓要教孙儿认字读史。咱们的戏不是为了捧谁,而是让每个普通人知道:你记得,就是史。”
李念颔首,随即展开一张舆图,指向上游一处标注红点的小城:“这里,是‘新影’最后的印坊据点,名为‘文渊坊’,表面隶属礼部工造司,实则专事《新贞元实录》雕版修订与批量翻印。沈无咎名录中标注,此处藏有原始篡改底稿,并设有地下密室,存放所有伪造家谱、墓志原件。”
医师陈七皱眉:“朝廷刚下令查封全国忆馆,他们必会加紧推进新书刊行,借此确立‘正统’话语。若再不毁其根基,十年之内,真相真将沦为异端。”
“所以,”李念声音冷而稳,“我们要亲自走进那座印坊。”
众人一惊。
“不是派人潜入,不是纵火焚屋。”她眼中闪过锐光,“是要堂而皇之地进去,买下它。”
“买?”三人异口同声。
李念嘴角微扬:“你们忘了?我父亲生前曾任边军粮秣督办,虽战死沙场,但他在江南仍有三处田产与一座钱庄股份,一直由旧部代管。昨夜信使带回地契与凭书,共计白银八万两,足可收购文渊坊及其附属书肆七家。”
老周激动得拍案而起:“妙啊!我们买下来,先照常印那伪书,再悄悄调换雕版??等他们发现时,满天下流传的已是真本!”
“不。”李念摇头,“我们不换版,我们加页。”
她取出一叠纸稿,正是最新修订的《补遗录?执灯者章》。“我们将这份名录、沈无咎供述、海外承灯图、七僧吞书壁画……全部编为‘附录’,冠以‘民间拾遗’之名,随《新贞元实录》一同发售。百姓买的是官定史书,翻开却见另类记载。他们会疑惑,会比对,会追问??而这,正是我们想要的。”
阿娥抚掌笑道:“好一招‘借壳传魂’!朝廷越推伪书,就越帮我们传播真相!”
计划即定,行动迅疾。七日后,一名自称“徽州书商”的妇人携巨款现身礼部工造司,言称欲购文渊坊以扩业。因裴文渊近日闭门养病,事务暂由副手处理,又见银票确凿、背景清白(实为传灯会多年经营的身份掩护),遂准予交易。
十日之内,产权过户完成。李念亲任“坊主”,任命老周为总刻师,陈七为账房先生,阿娥则率戏班入驻坊内乐厅,每日排演“劝善新戏”,吸引文人墨客前来观览。一时间,文渊坊竟成了京城新兴的文化雅集之所。
然而,平静之下,暗流汹涌。
某夜子时,李念正在密室校对新刻附录,忽觉窗外树影微动。她不动声色,轻轻推开一道窗缝,只见一人黑衣蒙面,正欲撬开地库铁锁。她冷笑一声,吹灭烛火,悄然绕至后院,与埋伏已久的陈七合力将其擒获。
摘下面罩,竟是原印坊一名老匠人,名叫赵伯通,曾参与《新贞元实录》初版雕刻。
“你说,为何背叛?”李念坐于案前,语气平静。
赵伯通低头不语,双手颤抖。
“你是被收买了?还是被人威胁?”
老人忽然抬头,眼中含泪:“我不是背叛……我是想毁了它!那本书……那本书不该存在!我亲手刻下每一刀,把李慎写成叛贼,把南宫萤写成妖妃……可我知道那是假的!我夜里做梦,全是他们在火里喊我名字!”
李念沉默片刻,问:“那你为何不早来投诚?”
“我不敢!”他哽咽道,“我妻儿还在他们手中!他们说,若我泄密,便让我全家暴毙街头!今夜我冒险进来,只想偷偷烧掉底稿……哪怕只毁一卷也好!”
李念起身,亲自解开他身上绳索。“你没做错什么。恐惧不是耻辱,沉默也不是罪过。真正该下地狱的,是让人不敢说话的人。”
她递上一杯热茶:“现在,你还愿意帮我们吗?不是为了赎罪,而是为了让自己以后能睡个安稳觉。”
赵伯通泪流满面,重重叩首。
自此,文渊坊内部彻底清洗,原有工匠中凡有良知者皆被吸纳进传灯会体系,其余可疑之人则以“年迈告退”为由遣散。与此同时,新版《新贞元实录》正式开印,封面依旧庄严,内容看似无异,唯独在末尾多出百余页“附录”,题为《贞元拾遗?野史存真》。
起初无人注意,直到某位翰林院编修购书归家,闲暇翻阅附录,竟发现其中一段文字与自己祖父日记完全吻合??那是一段关于贞元八年饥荒中百姓易子而食的惨状记录,早已被官方抹去。震惊之下,他连夜抄录全文,送至几位同僚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