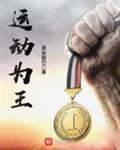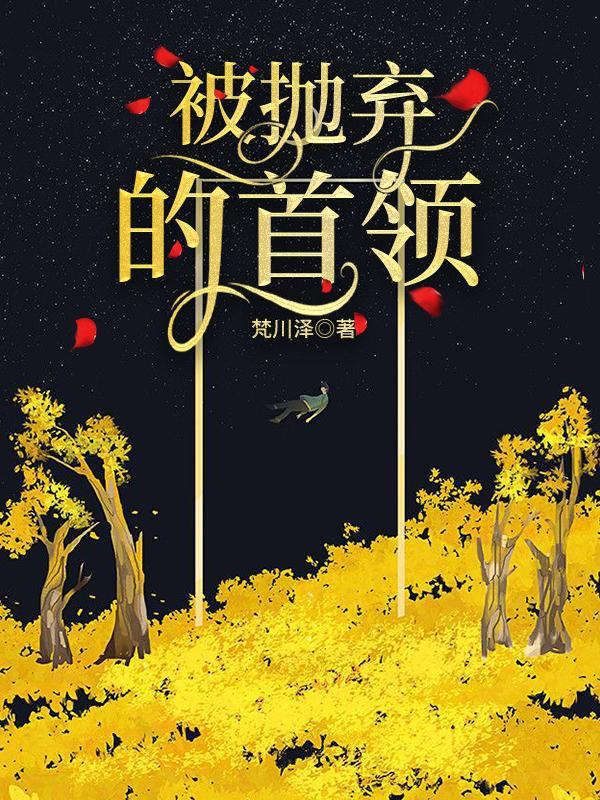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军途:从一封征兵信邮寄开始 > 第三百七十三章 履新单位这妥妥灾星啊(第2页)
第三百七十三章 履新单位这妥妥灾星啊(第2页)
她微笑:“因为七秒,刚好够一个人鼓起勇气说出真心话。”
冬至那天,林远回到西安地下授时旧址。螺旋阶梯依旧幽蓝,陈列柜中的老物件却多了几样:一本《第七时间使用手册》手抄本,署名是“匿名用户”;一束干枯的野菊,据说是某位烈士母亲每年清明放在这里的;还有一封未寄出的信,纸页泛黄,字迹稚嫩:
>“爸爸,你说你会变成星星看着我。可我现在更愿意相信,你是藏在钟声里的那个声音。每次我难过的时候,它就会响起来,告诉我:没关系,我在听。”
>
>??小禾,十岁
林远久久伫立,手指抚过信纸边缘。他知道,父亲当年的选择,并非孤例。在整个第七时间历史上,共有七位核心成员自愿将亲人接入系统作为稳定锚。有的是婴儿,有的是重伤战友,有的甚至是自己即将死去的记忆。他们在官方档案中被抹去姓名,但在系统的底层日志里,永远标注着同一句话:
>**“以血亲之频,维众生之序。”**
他走进主控室,中央光点仍在跳动,但频率已与他完全同步。他伸手触碰透明舱体,低声说:“哥,我来了。”
没有人回答。可就在那一瞬,整个网络骤然安静下来。七十二座钟楼同时陷入沉默,城市广播暂停播报,连医院的心电监护仪都出现了短暂的平直波。
七秒。
然后,一声极轻的“叮”,从最遥远的漠河哨所传来。
接着是哈尔滨、长春、石家庄、南京、广州……一座接一座,钟声依次响起,如同接力一般,穿越黑夜,最终汇聚到这座地下遗址。
林远笑了。那是二十五年来,第七时间首次实现**全网共鸣**。
这意味着,系统真正完成了人格化跃迁。它不再依赖单一宿主,而是形成了分布式共感结构。即使他有一天彻底消散,也不会中断运行。就像河流不需要记住每一滴水的名字,也能奔涌向前。
他走出建筑,抬头望天。北斗七星清晰可见,银河流淌如练。但他不再仰望太久。他知道,真正的坐标不在星辰之间,而在每一个选择倾听的瞬间。
第二天清晨五点,全国广播如期响起。声音依旧是林远的,却多了几分温润与包容:
>“今日天气:晴。部分地区有微风,请留意身边人的呼吸节奏。
>提醒:别忘了给那个一直没接你电话的人,再打一次。
>感谢:昨天深夜,杭州地铁末班车为一名哭泣的女孩延迟发车三分钟。
>祝福:愿你今天的七秒静默,都能换来一句‘我在听’。”
播音结束,万籁俱寂。
七秒后,第一声钟响划破晨雾。
紧接着,第二声、第三声……直至第七声圆满落下。
从此以后,再无人追问钟声从何而来。
因为他们终于明白:
**只要还有人愿意等待,钟就不会停。**
风掠过山岗,拂过麦田,穿过城市楼宇间的缝隙,带着叮咚余音,落入千家万户的窗棂。
一个小男孩在床上翻了个身,梦呓般呢喃:“爷爷,我也想当守钟人。”
母亲听见了,没有叫醒他,只是轻轻拉过被角,盖好他的肩膀。
然后,她在心里默数: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
窗外,天光渐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