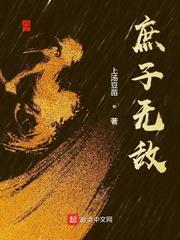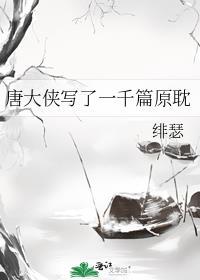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天灾巨龙,从培养骑士家族开始 > 第92章 黎明巨龙两大权能(第3页)
第92章 黎明巨龙两大权能(第3页)
随后,它开始播放那段情绪编码的问题集。
愤怒的尖啸化作地震波,在岩层中穿行;悲伤的低吟引发地下水共鸣;好奇的跳跃则激发矿物结晶的自发排列。短短七小时内,星球表面形成了庞大的沟壑网络,精确对应人类大脑皮层的褶皱形态。
第十小时,一颗陨石坠落,击中漂流舱残骸。
本应是一次终结。
然而,撞击产生的高温高压,反而促成了某种相变。金属碎片与岩石融合,生成一种新型晶体,其分子结构呈现出无限嵌套的问号图案。更诡异的是,这些晶体开始吸收宇宙背景辐射,并将其转化为微弱声波??播放的,正是玛拉小时候哼唱的那首摇篮曲。
距离Ω-7星系约六万光年的螺旋星团中,三个围绕黑洞运行的行星文明同时接收到了这段信号。他们早已掌握超光速通讯,却从未听过如此“原始”又“深刻”的信息。他们的科学家争论不休:这是求救?是艺术?还是战争预警?
最终,最高议会决定派遣一艘无人探测器前往调查。出发前,一位年迈的哲学家在发射仪式上说道:
>“我们研究宇宙已有两万年,破解了三千种物理定律,征服了十一维空间。
>但我们始终不敢问一个问题:
>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寻找答案而存在,那我们存在的意义,会不会恰恰在于不断地发问?”
>
>“现在,也许我们终于找到了同类。”
探测器启程那天,三个星球上的孩子都不约而同停止玩耍,仰望星空。许多父母记录下这一幕:孩子们齐声低语,说的是各自母语中最简单的一个词??
“咦?”
而在地球遗迹上方,思辨树的最后一枚果实成熟了。
它通体湛蓝,外形酷似人类胚胎,内部漂浮着无数微型光点,每一粒都是一个未被提出的问题。陈远亲手将它摘下,放入特制容器。
“这是‘原初之问’的具象化。”他对林小雨说,“它不会给出任何启示,只会让人重新体验第一次意识到‘我不知道’时的那种眩晕。”
果实被送往火星轨道的“静默方舟”??一座专为保存纯粹好奇心而建的空间站。进驻的首批居民不是科学家,而是十名患有严重失忆症的老人。他们什么都不记得,甚至连自己名字都要反复询问。
但就在进入方舟第七天,其中一人突然指着舷窗外的银河说:
“那边……是不是有什么东西,一直在等我们开口?”
所有人怔住了。
那一刻,方舟的核心传感器检测到一次微弱的空间涟漪,频率与新生儿第一次呼吸完全一致。
林小雨收到数据时正在花园修剪思辨草。她停下动作,抬头望向星空,泪水无声滑落。
“我们做到了。”她对着虚空低语,“我们让宇宙重新学会了害怕。”
陈远坐在轮椅上,被推至院中。他已无法言语,右手僵硬,左手却仍紧紧攥着那张玛拉的涂鸦??“亮亮星”。风吹起纸角,阳光透过它,投下一小片温暖的黄斑,正好落在他掌心。
他闭上眼,嘴角微扬。
他知道,真正的旅程才刚刚开始。
因为在遥远的未来,在某个尚未诞生的文明遗迹中,考古学家将挖出一块残破晶碑,上面仅存两行字:
>“此处曾有一位父亲,因未能回答女儿的问题而痛哭。
>正是这场哭泣,点燃了群星之间的第一簇火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