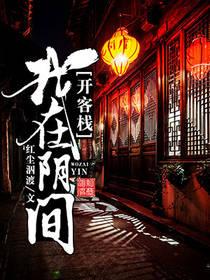笔趣阁>这个明星正得发邪 > 第446章 曾经的你(第2页)
第446章 曾经的你(第2页)
一个月后,江曜峰出现在一家地下Livehouse门口。
这里远离市中心,藏身于老城区巷弄深处,招牌锈迹斑斑,写着三个褪色大字:“回声”。他曾听腾智辉提起过这个地方??据说每年只开放七晚,专供那些不愿被聚光灯照耀的灵魂试唱。
今晚,是第七夜。
他推门而入,空气中弥漫着陈旧木地板与咖啡渍混合的气息。舞台不过两米见方,灯光简陋,观众席稀稀落落坐着不到百人。有人闭目聆听,有人低声交谈,没人拍照,也没人录像。
台上,一个男人正在弹吉他,嗓音低沉地唱着一首民谣。曲终,掌声寥寥。
主持人拿起话筒:“感谢张野。下一组表演者,请欢迎??‘无名’组合。”
台下响起几声轻笑:“又是个取假名的吧?”
江曜峰却突然坐直了身体。
因为走上台的两个人,他再熟悉不过。
秦月穿着牛仔外套和帆布鞋,怀里抱着一把木吉他。陆燃则背着电箱琴,脸上带着久违的松弛笑意。他们没有介绍自己,只是相视一笑,便同时拨动琴弦。
前奏一起,全场安静。
这不是任何一首已知的作品。旋律简单却极具穿透力,像春风吹过冻土,唤醒沉睡的根脉。秦月开口,声音依旧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涩感,但正是这份未经修饰的真实,让人心头一颤。
>“我曾把名字埋进雪里,
>怕被人认出哭泣的模样;
>我曾把歌声锁进别人胸膛,
>像寄居的鸟,不敢独自飞翔……”
陆燃接过第二段,声音低沉如诉:
>“我替你唱过千百遍黄昏,
>每一句都是你的灵魂在震颤;
>如今你终于站在光下,
>而我愿退回shadows之间。”
当两人合唱第三段时,音浪如潮水般涌起:
>“不必谢我,不必回头看,
>你走的每一步,本就是你该走的路;
>若有来生我还愿做你的影,
>只要你能大声说出:这是我写的歌。”
歌曲结束,全场静默。
足足五秒钟后,才有人缓缓鼓掌,接着是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最后,整个空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有人站起来,有人抹着眼角,还有人掏出手机想录视频,却被旁边的人轻轻按住手臂:“别拍了,这是属于他们的时刻。”
秦月低头笑了笑,说:“这首歌叫《影子》,是我们写给彼此的告别信。”
台下一片抽泣声。
江曜峰默默起身,悄悄退到场外。他拿出手机,给腾智辉发了条信息:“你说得对,她从来就没输过。”
***
一周后,国家音乐厅发布公告:应广大观众请求,原定于下月举行的“归声”巡回演唱会首站,正式升级为国家大剧院专场演出,并同步举行全球直播。
与此同时,央视音乐频道推出特别纪录片预告片《谁是顺其自然》,片头第一句旁白便是:
>“在这个人人都急于被看见的时代,有些人选择隐身,只为等一句真话。”
而在某座南方小城的老房子里,一位老人颤巍巍地打开电视,调到音乐频道。屏幕上正播放着秦月在Livehouse演唱的画面。她笑着对观众说:“谢谢你们,还记得我的声音。”
老人泪流满面,嘴唇微动,却发不出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