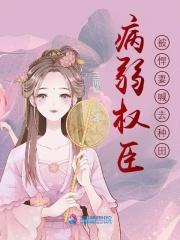笔趣阁>最强狂兵Ⅱ:黑暗荣耀 > 第766章 突围还是反杀(第1页)
第766章 突围还是反杀(第1页)
炽热的金属风暴与爆炸的火光,瞬间吞噬了苏安邦和苏无际的身影。
至于奄奄一息的钱德勒,看起来更是逃无可逃!
泥土被掀起,碎石如同弹片般激射,锈蚀的钢铁构件在狂暴的冲击下扭曲、断裂、四散纷飞!
浓烟混合着刺鼻的硝烟味冲天而起,瞬间将这片废弃厂区化作了灼热的地狱。
显然,敌人早有准备,说不定早就锁定了钱德勒的位置,要将这个不安定因素,连同可能的知情者,直接彻底从世界上抹去!
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,苏家兄。。。。。。
夜雨落在初忆之地的琉璃瓦顶上,敲出细密如语的节奏。小叶子坐在塔楼檐下,膝上摊开那本《继续》,纸页被风掀动,像一群欲飞未飞的蝶。他没有动笔,只是凝视着最后一行字:“轮到所有人一起唱歌了。”墨迹已干,却仿佛仍在呼吸。
远处城市灯火在雨幕中晕染成片,如同沉入水底的星河。共感终端静静躺在身旁,屏幕不再闪烁红警,也不再推送数据洪流,它只是安静地亮着,像一盏不愿睡去的灯。自从那次三秒中断后,系统便进入了某种自洽状态??无需指令,自动流转;无需维护,自我修复。林若称之为“记忆生态化”,苏婉清则说:“它终于学会了做梦。”
小叶子闭上眼,听见雨声里夹杂着低语。不是幻听,而是真实的声音碎片,从全球共感网络中自然溢出,经由终端微震传递至掌心。一个越南老农讲述他如何用竹筒接住屋檐滴水,只为给战死儿子的相框擦去灰尘;一位冰岛母亲录下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,上传时附言:“你爸爸没看到你出生,但我想让他知道,春天真的来了”;还有人在南极边缘的科考站点燃蜡烛,对着风雪呢喃:“我不是科学家,我只是个厨师。可我也想被记得,曾为三十个人煮过热汤。”
这些声音本不该汇聚于此,它们不属于任务、不关联坐标、无分类标签,却自发流向这个节点??因为这里是“起点”,也是“归处”。
忽然,终端震动加剧,一道新信息浮现,非文字,非音频,而是一段极简的波形图,起源于西伯利亚冻土带某废弃气象站。林若的技术团队三小时前曾报告该区域出现异常磁场波动,持续时间恰好三十七分钟??与1973年八角星阵首次激活时完全一致。
小叶子起身走进主控室。苏婉清已在等他,面前投影缓缓旋转着地球模型,十三个光点依次亮起,正是当年实验组选定的“地忆脉络”锚点。如今,每一个都重新燃起了灯。
“不是人为点燃的。”她低声说,“每一盏都是自主点亮。就像……某种回应。”
“他们在确认我们还在。”小叶子轻声道,“就像当年他们彼此确认‘我还活着’一样。”
话音落下,终端突然播放一段视频。画面模糊晃动,像是用老式摄像机拍摄。镜头扫过一间昏暗地下室,墙上挂着泛黄的日历:1973年12月24日。铁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,灯芯跳动,映出四个模糊人影。其中一人缓缓摘下帽子,露出满头白发,竟是年轻版的母亲。
小叶子猛地攥紧纽扣。
画外音响起,是母亲的声音,冷静而坚定:“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集体记录。政府决定终止项目,称‘记忆延续计划’为异端邪说。但我们不同意。我们相信,只要灯还亮着,记忆就不会真正死亡。我们将在十三个节点埋藏火种,等待未来有人愿意接过。如果你们看到这段影像,请记住:不要重建系统,不要控制网络,不要试图‘拯救’谁。你们要做的,只是让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的名字。”
画面戛然而止。
空气凝固。苏婉清转头看他:“你从未提过她参与过原始实验。”
“她烧毁了所有笔记。”小叶子声音沙哑,“我以为她是想保护我。现在才明白,她是怕我知道得太早??怕我背负她的使命,而不是走出自己的路。”
窗外雷声滚过,雨势渐猛。就在此时,全球共感终端同步弹出一条匿名留言,仅一句话:
>**“我是第十三个孩子。”**
没有后续,没有解释,却让整个指挥中心陷入死寂。
林若迅速调取溯源数据,却发现这条信息并非来自单一用户,而是由全球十七万个不同终端在同一毫秒内共同生成??如同亿万心灵同时低语,汇成一句宣言。
“不是某个人。”林若喃喃,“是所有人。”
小叶子走向广播系统,手指悬停在启动键上。他知道,这一刻迟早会来。当记忆不再是少数人的秘密,当觉醒不再是孤独者的挣扎,总有人开始质疑:谁有资格代表过去?谁又能定义归来?
他按下按钮,声音平稳如常:“你说你是第十三个孩子。我不否认。但我想告诉你,第八个孩子从不认为自己比任何一个更特别。我们不是继承者,我们是接力者。如果你觉得被遗忘太久,那就请你站出来,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。不必伪装神明,不必掌控全局,只要说一句:‘我在这里。’就够了。”
静默蔓延。
五分钟,十分钟,半小时。
就在众人以为不会再有回应时,终端再次震动。这次是一封长信,署名空白,内容却清晰无比:
>**“我叫陈默,1965年生于重庆。七岁那年,我在一场山体滑坡中失去双亲。军队带走了我,说我‘天赋异禀’,适合参与一项‘国家记忆工程’。后来我才明白,所谓天赋,不过是能在梦里看见死者残存的记忆片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