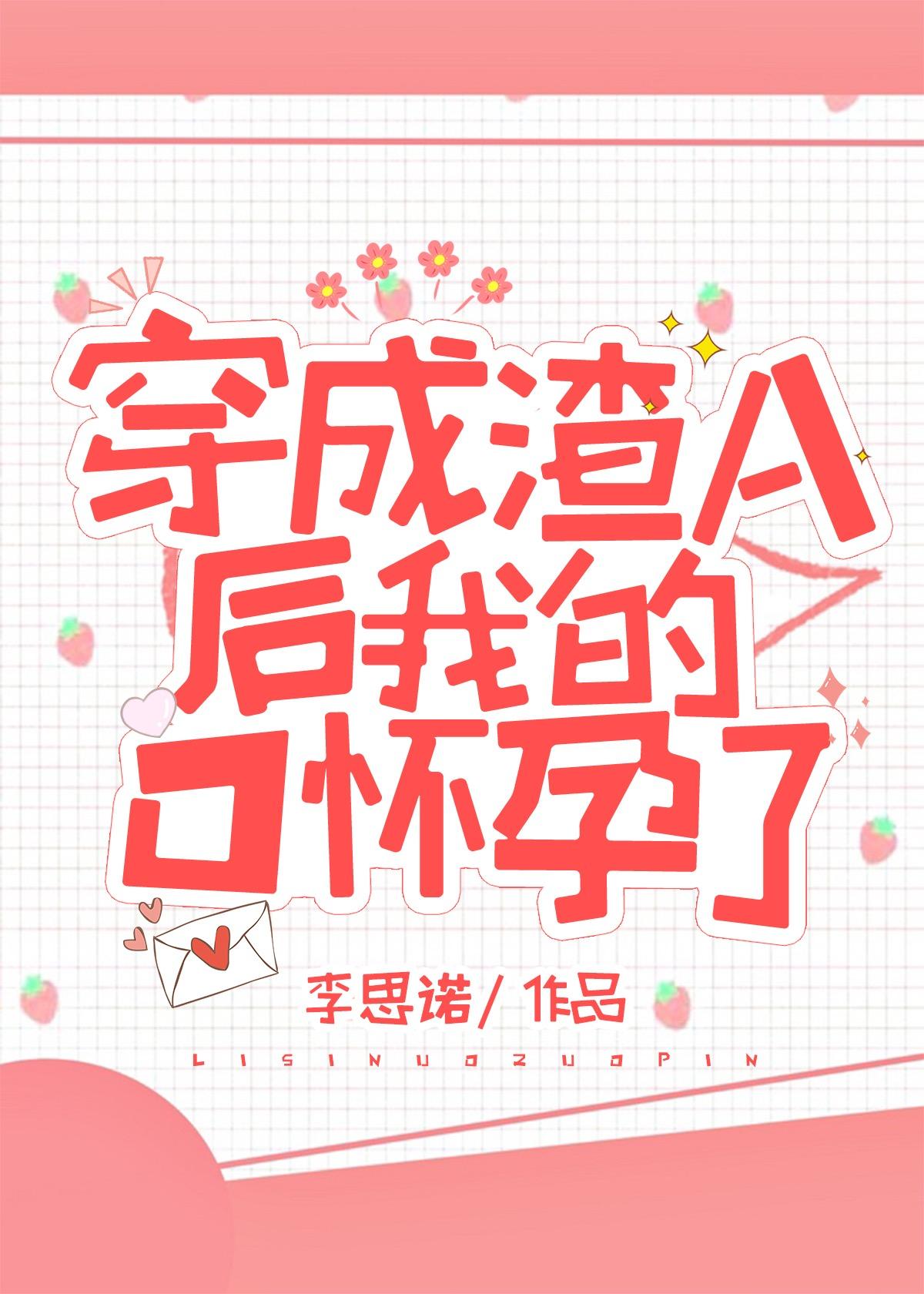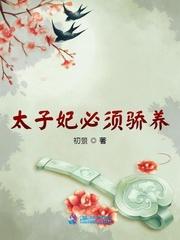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出宫前夜,疯批帝王后悔了 > 第486章 倾倒万千少女(第3页)
第486章 倾倒万千少女(第3页)
“好名字。”她牵起小女孩的手,带她来到忆鉴镜前,“闭上眼睛,想着你父亲的样子,然后告诉我,你想对他说什么。”
小女孩乖乖照做,小声说:“爹爹,我不怕。我已经学会写字了,老师教我们写‘真’字。你说过要说真话,所以我每天都写一百遍……你要是听得见,就响一下铃好不好?”
话音刚落,屋檐下一枚铜铃,轻轻晃了一下。
叮。
小女孩猛地睁眼,眼泪夺眶而出:“是他!真的是他!他听见我了!”
她母亲也在旁边泣不成声:“这孩子自从父亲被抓后就没笑过……可今天,她笑了。”
此后数月,络绎不绝的人前来求见。
有寻找失散亲人的,有想确认某段记忆是否真实的,也有单纯来听一听“过去的声音”的。晚芜从不拒绝,也不收费,只让他们在离开前做一件事:摇一次铃,说一句真话。
渐渐地,这座小小的铃屋成了民间心中的圣地。
有人称她为“昭明夫人”,有人说她是“活的史官”,更有人悄悄传言:每当月圆之夜,若静心聆听,能听到三百个声音齐声诵读《真实录》,那是亡魂们在替人间守夜。
一年后的春分,记忆碑林落成。
晚芜受邀出席仪式,但她只是远远站在人群之外。当第一块石碑被揭开,露出密密麻麻的名字时,她转身离去。
程砚追上来:“你不进去看看吗?你的名字也在上面,排在第一位。”
“我不需要被铭记。”她说,“守夜人的职责不是成为英雄,而是让每个人都敢于成为讲述者。”
她回头望了一眼那片碑林,阳光照在冰冷的石头上,映出无数个名字的影子。
“你看,”她微笑,“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。”
回到骊山,她发现门前多了一串新铃。
是那位叫阿阮的小女孩送来的,用废旧铁片亲手打磨而成,虽然粗糙,却刻着两个字:**“不瞒”。**
她将它挂在最高处。
风起时,新铃与旧铃交响成曲,清越悠远,仿佛穿越百年时光,回应着最初那一声微弱的啼哭??
那一夜,春雨又至。
长安城万家灯火,每一户门前都亮起了灯笼,每一扇窗后都传来低语声。人们讲述着祖辈的故事,孩子们认真记下每一个细节。
而在紫宸殿旧址,一群年轻的史官正彻夜誊抄新编的《贞元实录》。
当他们写到“裴晚芜拒登帝位,归隐骊山,终身未嫁”时,一位年轻学士忽然抬头问:“先生,她真的不爱权势吗?”
老史官放下笔,望向窗外连绵的灯河,缓缓道:
“她爱的不是权力,而是自由??让人说出真相的自由。而这,比皇位更难获得,也更值得守护。”
雨停了。
东方泛起鱼肚白,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,洒落在骊山之巅。
那满树铜铃,在晨光中轻轻摇曳,发出细碎而坚定的声响。
一声,两声,千声万声……
如同永不熄灭的星火,照亮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