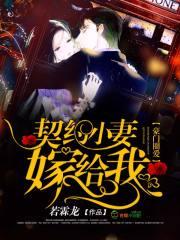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大明第一国舅 > 第679章 塞王(第1页)
第679章 塞王(第1页)
庞大的队伍开始休整、换装,准备着入城的一系列事情。
肯定是要衣甲鲜明、旗帜招展的入城,而不是灰头土脸的犹如散兵游勇。
走了两个多月了,大家都有些疲惫。
邓氏端来饭菜,有些不舍,“舅舅。。。
夜雨如丝,悄无声息地洒在玉牒库的青瓦之上,滴答声与檐下铜铃轻响交织成一片。朱?坐在案前未动,手中那支狼毫笔早已干涸,可他仍紧握不放,仿佛一松手,连这点微弱的坚持也会随风而去。马寻已走,只留下半壶冷酒和一句“明日再来”,却像一把钝刀,在他心上反复磨刮。
他低头看着那页写满“悔过”二字的玉牒,墨迹被水珠晕开,竟似泪痕。他忽然笑了,笑声低哑,惊得屋角一只灰雀扑棱飞走。他笑自己竟会为一句话、一杯酒、一段往事而动摇??他朱?生来便是亲王,母妃是皇后,父皇是天子,舅舅不过是个外戚,凭什么教他如何做人?
可笑归可笑,胸口却压着一块石头,沉得喘不过气。
窗外雷声隐隐,宫墙深处传来更鼓三响。朱?终于起身,将那页玉牒缓缓卷起,放入漆匣,锁进柜中。他走出玉牒库时,雨势渐大,雨水顺着屋檐倾泻而下,如帘幕垂落。他没有撑伞,任冷雨打湿袍角,一步步踏过积水的石阶,走向楚王府所在的西六所。
翌日清晨,雨歇云散,宫苑蒸腾起薄雾。朱?醒来时头昏脑涨,昨夜淋雨染了风寒,额头发烫,婢女端来姜汤,他挥手打翻,瓷碗碎裂一地。邓氏闻讯赶来,见他面色潮红,心疼不已:“七爷,您这是何苦?昨儿个又去玉牒库了?”朱?闭目不语,只从唇缝挤出一句:“别管我。”
邓氏叹气,亲自绞了热帕敷在他额上,低声道:“姑母昨日派人来问,说您这几日未曾请安……她担心。”朱?猛地睁眼:“她还管我?她眼里只有规矩、责任、祖宗法度!我是不是她亲生的,她都未必在乎!”话音未落,喉头一甜,竟咳出一口血来。
邓氏大惊,忙唤太医。御医诊脉后摇头:“忧思过重,肝火犯肺,需静养避扰。”开了几味清热疏郁的药,叮嘱不可劳神动怒。朱?听罢冷笑:“我不过想做点事,怎么就成了‘忧思过重’?雄英一个十岁小儿都能执掌宗正院,我堂堂亲王反倒连句话都说不上?”
邓氏垂泪道:“七爷,您忘了娘娘昨夜说的话?她不是不疼您,只是更怕您走歪……”朱?怔住,良久才喃喃道:“我若真走歪了,她还会认我这个儿子吗?”
午后,阳光破云而出,照在宫墙金瓦之上,熠熠生辉。朱?勉强坐起,命人备轿,执意入宫请安。邓氏劝不住,只得命人加厚衣裳,亲自随行。
至坤宁宫外,恰逢朱标携朱雄英自东宫议事归来。朱雄英见朱?脸色苍白,关切上前:“七叔身子不适?”朱?勉强一笑:“无妨,来看看母妃。”朱标打量他一眼,眉头微皱:“你瘦了。这几日都在玉牒库?”朱?点头。朱标轻叹:“雄英虽年幼,但马寻与李贞皆老成持重,你不必挂怀。”语气平和,却隐含警告之意。
朱?心头一刺,正欲答话,忽听殿内传来马秀英声音:“让他进来。”
朱?整衣入内,跪拜于地。马秀英端坐榻上,手中仍是那件粗布短褐,针线未停。她看也不看他,只道:“病了还往宫里跑,是要我心疼你,还是逼我再训你?”
朱?伏地不起:“儿……知错了。”
马秀英手中的针微微一顿,抬眼看他:“错在哪?”
“儿以为,小宗正院是权柄,是地位,是能让我立身于诸王之上的阶梯。儿争它,是为了证明自己不输任何人。”他声音颤抖,“可昨夜在玉牒库,我想了一夜。那些名字,不只是名字……它们是一个个人,一条条命。我若执掌,一字之差,便可能毁人一生。儿……不敢了。”
马秀英放下针线,起身走到他面前,伸手抚他发鬓,指尖微颤:“你终于明白了。”她声音极轻,却如钟鸣震耳,“你父皇打天下,靠的是铁血;我守中宫,靠的是仁心;而你舅舅守玉牒,靠的是敬畏。权力不在大小,而在用它的人心中有没有底线。”
朱?泪如泉涌,伏地痛哭:“儿险些……成了罪人。”
马秀英扶他起身,柔声道:“起来吧。你还年轻,犯错不可怕,可怕的是不知回头。”她顿了顿,“明日宗正院有例会,你去旁听。不必发言,只需记住??每一个名字背后,都有一个家。”
次日辰时,朱?换上素色常服,低调入宫。宗正院设于奉先殿侧院,院中古柏森森,碑石林立,皆刻历代宗室名录。朱雄英已在堂中,正与马寻、李贞核对一支远房宗支的婚嗣记录。见朱?进来,众人略显惊讶,朱雄英却起身相迎:“七叔来了,请坐。”
朱?落座末席,默默聆听。议题是一桩陈年旧案:洪武十三年,一位旁支出嗣子弟因户籍错录,被剥夺爵位继承权,其子流放云南,至今未归。如今其孙上书请复籍,需查证原档。
李贞翻开泛黄卷册,叹息道:“当年档案残缺,又逢胡惟庸案动荡,许多记录遗失。若无确证,难予恢复。”
朱雄英翻阅呈文,忽然抬头:“舅舅,我记得玉牒副册曾在北库另存一份,是否可查?”
马寻点头:“确有其事,但北库多年未启,恐有虫蛀霉变。”
“那就去查。”朱雄英语气坚定,“一人之冤,关乎三代荣辱。不能因麻烦就不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