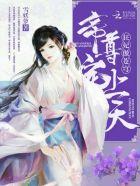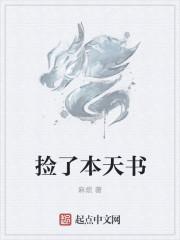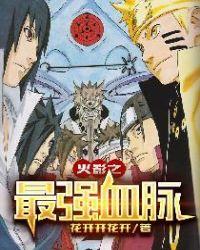笔趣阁>众仙俯首 > 第452章 高手果然是高手(第2页)
第452章 高手果然是高手(第2页)
>“未时,你将跪下,不是因为伤,而是因为心痛。”
>“申时,你会对我说:‘求你,让我记住这些话。’”
每一句落下,现实便随之扭曲。裴烈的剑突然脱手,插入泥土;右翼战马果然受惊,践踏己阵;他的目光渐渐涣散,仿佛被拉回某个遥远的冬夜。当他听到“母亲为你暖手”时,整个人剧烈颤抖,单膝触地。
“不可能……”他嘶声道,“你怎么会知道?那是我七岁的事……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……”
“因为那句话从未真正消失。”沈知意走近他,声音轻柔,“它一直在等一个能听见的人。”
她伸出手:“现在,你愿意说出来了么?”
裴烈仰头望着她,眼中金丝寸寸断裂,如枯藤崩解。他张口,发出多年未曾使用的真实嗓音,沙哑而颤抖:
“娘……我记得了。你说……‘孩子,别怕说错话,怕的是不敢说。’”
话音落,他身后所有士兵的铠甲上的镇言符文同时剥落,化为灰烬。千军倒戈,兵器尽弃。
启言院门前,只剩沉默。
春分当日,无雪,无雨,天地静得仿佛屏息。
沈知意独坐院中老槐之下,面前摆着七十七枚竹简。她逐一展开,以心头血为墨,批注解译。当她读到第十三简时,笔尖骤然凝滞。
>“金箔非物,乃门钥。持者非人,乃‘声之形’。九渊不开,因言未净。”
她心头一震。阿砚手中的金箔,从来不是实物?而是“声音凝成的钥匙”?那他为何要呼唤它?又为何藏身九渊?
她猛然想起《残语志?外篇》中一段被水渍遮蔽的记载:“丙戌年,南陵祭司以声塑形,令亡魂执言而行,谓之‘代述者’。”??所谓“代述者”,并非活人,而是由纯粹言语凝聚成的灵体,承载某人未尽之言,游走世间,直至被接续。
难道……阿砚早已不在人间?他之所以能穿越九渊、避过追杀,是因为他已化作“声之形”?而那金箔,正是他最后一句真话的具象?
她抬头望天,春分阳气升腾,天地交汇之处,隐隐有钟声回荡。这一次,不是来自万言钟,而是来自更高处??仿佛苍穹本身,正在震动。
忽然,小女孩跑来,手中紧握那半块木炭,眼睛亮得惊人:“姐姐,哥哥说,他在等一把能听见他的琴。”
“琴?”沈知意一怔。
“不是琴,是‘情’。”小女孩摇头,“他说,只有真心想听的人,才能奏响他。”
沈知意浑身一震。
她终于明白了。金箔不是钥匙,**心**才是。唯有以真心为弦,以倾听为弓,才能奏出那扇天门的开启之音。
她起身,走向启言井。井水清澈如镜,倒映星空。她取出发光的“言髓”坛子,将其缓缓倾入井中。乳白的液体沉入水底,瞬间扩散,整口井开始发出低频共振,如同大地的心跳。
她闭目,开始吟唱。
不是童谣,不是咒语,而是最原始的、属于人类的第一句话??一个母亲对孩子说的“不怕”。
音波入井,水面骤然升起一道光柱,直冲云霄。光中浮现出无数面孔:有南陵殉言者,有归墟守书人,有微声堂叛徒,甚至还有那些被鸦群吞噬的疯癫村民……他们全都张着嘴,却无声。他们在等待,等待有人替他们说出那句未能出口的话。
沈知意一一回应。
她为哑女踏出“步文”,为疯汉诵出“天将雨”,为囚徒喊出“冤”字,为死者念出“安息”。每说一句,便有一道光脱离光柱,升腾而去,如星归天。
当她说出第一百零八句时,九渊方向忽然传来回应。
一声琴音。
不属五音,不循十二律,却直击灵魂。那音色像是青铜与血肉摩擦,又似星光坠入深潭。紧接着,第二声、第三声……连成一曲,正是她童年时,阿砚为她弹过的那首无名小调。
她泪流满面,对着虚空大喊:“阿砚!是你吗?”
琴声戛然而止。
风静,云开,月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