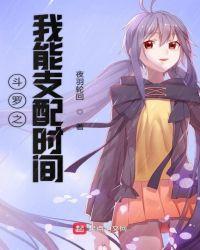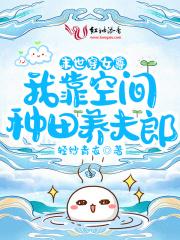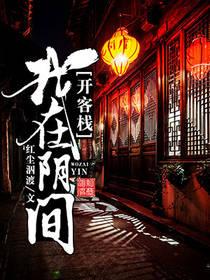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千禧:我真不想当大导演 > 番外1 林无非小朋友的日记(第2页)
番外1 林无非小朋友的日记(第2页)
当晚,林有攸参加了村里组织的“围炉夜谈”。十几户人家挤在一间暖房里,围着火炉,轮流播放他们录下的声音。有老人讲述三十年前如何徒步百里求医救活冻伤的儿子;有少年坦白自己偷偷喜欢同村的女孩却不敢开口;还有一个五岁小女孩,奶声奶气地说:“我希望月亮每天都能看见我睡觉,这样它就不会孤单了。”
没有人嘲笑,没有人打断。每一段结束,大家都会轻轻鼓掌,有人说一句“听见了”,或“你也一样”,或简单一个“嗯”。
那一刻,林有攸感到一种久违的宁静。这不是什么宏大叙事,也没有媒体镜头,更没有掌声与荣誉。但这才是“回声计划”最初的模样??不是拯救,而是陪伴;不是治疗,而是见证。
第二天清晨,他独自爬上村子背后的山坡,找到了徐建国所说的山口。那里立着一块临时木牌,上面贴着打印纸:“致所有未曾说出的话:你们终将被听见。”
他从背包里取出一枚U盘,插进防水盒中,埋进石堆底部。里面存着那个小男孩的录音,以及全国两千三百一十七个“倾听点”收集到的第一句倾诉,按时间顺序剪辑成一段长达六小时的声音长河。
“有一天,”他对风说,“我们会在这里建一座真正的纪念碑。不用大理石,也不用青铜,就用回收的旧录音机外壳熔铸而成。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刻上去,让风吹过缝隙时,奏出属于普通人的交响。”
回到成都已是深秋。城市依旧喧嚣,地铁口流动广告屏滚动播放着最新电影预告,其中一部赫然写着《听见》,导演署名“林有攸”。他愣了一下才想起来,那是半年前答应朋友客串监制的一部青春片,讲的是两个聋哑少年通过手语诗寻找自我的故事。当时他只提了些建议,没想到最后海报上竟打了他的名字。
他摇摇头,正要走进小区,却被一个身影拦住。
是个年轻人,二十出头,穿着洗得发白的卫衣,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A4纸。
“林……林老师?”他声音颤抖,“我是陈默,就是……就是两年前在网上发过‘想消失’的那个。”
林有攸立刻认出了他。那是“回声计划”最早接到的高危预警之一。一个大学生连续三个月在匿名论坛发布自我贬损言论,关键词包括“无价值”“拖累家人”“不如死去”。系统捕捉到后自动推送干预方案,团队连夜联系学校心理中心介入。后续跟踪显示,该生接受了长期咨询,并逐渐恢复社会功能。
“我……我一直没敢当面道谢。”陈默低下头,声音哽咽,“那时候我真的准备跳楼了。就在那天晚上,我收到了你们平台寄来的‘情绪急救包’,里面有笔、本子、耳塞,还有一张卡片,写着‘你不需要完美,只需要存在’。我就坐在阳台边缘,一边哭一边写下了这辈子第一封给自己的信……后来,我就没再往下跳。”
林有攸静静听着,眼眶微热。
“我现在在做志愿者,”陈默抬起头,眼里闪着光,“在高校心理社团带小组讨论。我把那张卡片复印了很多份,送给每一个愿意说话的同学。”
林有攸伸出手,用力握住他的手腕:“你救了不止你自己。”
那天晚上,他破例喝了点酒。酒至微醺,他打开尘封已久的个人社交账号,写下一条动态:
>有人问我,为什么不做电影了?
>其实我没停,只是换了银幕。
>学校的图书角、社区的茶水间、高原的山口、牧民的帐篷……
>每一次有人鼓起勇气开口,
>都是一场只属于两个人的放映。
>而我,只是恰好在场的那个,
>愿意按下‘录音’键的人。
凌晨两点,评论区已涌进上万条留言。
有人写道:“昨天我用了单位楼下的‘倾听亭’,说完我妈出轨的事,哭了四十分钟。出来时发现门口放着一杯热奶茶,便签上写着‘你说过了,现在轮到生活对你温柔一点’。”
另一人说:“我女儿自闭七年,昨天第一次主动拿起家庭倾听包里的录音笔,说了一句‘爸爸,我想吃饺子’。我和老婆抱在一起哭了好久。”
还有人附图:一张泛黄的纸条,上面歪歪扭扭写着“今天有人听我说话”,落款日期是三天前,署名“王桂香,78岁,独居”。
林有攸一条条看完,最终关掉手机,走到阳台上。
江风依旧,桥灯如星。
他忽然想起大学时电影课教授说过的一句话:“伟大的导演,从不试图掌控观众的眼泪,而是创造让人敢于流泪的空间。”
那时他以为这是艺术的真谛。如今才懂,这何尝不是生活的答案?
有些人一生都在等待一个可以安心崩溃的地方。而我们要做的,不过是悄悄递上一支录音笔,然后蹲下来,轻声说一句:
“你说,我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