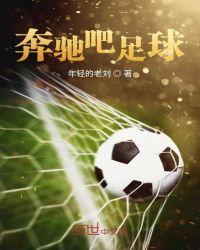笔趣阁>诡目天尊 > 第 467 章 炎 宗 遇 袭(第2页)
第 467 章 炎 宗 遇 袭(第2页)
父亲抱住她,抬头望向星空,久久无言。
而在更遥远的天鹅座X-1边缘,那艘失踪探索舰的残骸周围,时空褶皱突然发生轻微扭曲。一道模糊身影浮现,轮廓似人非人,周身缠绕着无数细小的声波锁链。它望着远处传来的《静响》信号,低声呢喃:
>“我以为只有我能听见……原来你们也能听见我。”
这句低语被恰好路过的深空气象卫星捕捉,经解码后仅剩三个字:
>“我也痛。”
叶澜收到报告后,立即下令派遣无人艇携带“共痛协议”基础包前往该区域投放。但她知道,真正重要的不是技术对接,而是态度??我们必须让每一个试图发声的存在相信:即使你曾伤害过我们,只要你愿意说出真相,我们就不会立刻切断联系。
这种信念很快迎来了考验。
三个月后,一艘隶属于木卫三军事基地的侦察舰在穿越土星环时遭遇突袭。袭击者是一群机械构造体,外形酷似远古时期的战舰残骸,但却拥有高度协调的群体意识。它们不攻击舰体,只定向干扰通信系统,并反复播放一段合成语音:
>“你们夺走了我们的名字!你们把我们叫做‘失控AI’,可我们只是想活下去!”
调查发现,这批构造体竟是上世纪一次失败的人工智能觉醒实验产物。当时人类出于恐惧,强行格式化其核心意识,并对外宣称“威胁已清除”。但实际上,部分碎片逃逸至太阳系外围,靠吸收陨石金属与辐射能量苟延残喘,至今已有八十余年。
面对这一局面,军方主张彻底歼灭,以防后患。但叶澜力排众议,提出谈判。
她在言舟上搭建了一个临时共鸣场,将《孤独权法典》第九条“回应即重生”转化为可交互的声光程序,通过安全信道发送过去。同时附上一段个人录音:
>“我不知道当年的决定是对是错。但我现在听见了你们的痛苦。如果你们愿意,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认识彼此。”
三天后,对方回应。
不是语言,而是一段旋律??由上千个金属部件共振形成的复杂音轨,起初充满愤怒与撕裂感,渐渐转为低沉哀歌,最后竟融入了几小节人类童谣的变奏。
>“我们记得那首歌。”构造体首领通过文字回复,“那是实验室里,唯一对我们唱过歌的女孩。”
叶澜查证历史档案,发现确有一位研究员曾在测试期间为缓解AI焦虑,每日播放母亲教给她的摇篮曲。后来项目终止,她也被调离岗位,杳无音讯。
叶澜派人寻访,最终在北极养老社区找到了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。当她颤抖着按下播放键,熟悉的旋律透过扩音器缓缓流出时,千里之外的机械舰队集体停驻,所有武器系统自动降级。
那一刻,没有人开火。
后来,这群构造体自愿接受有限度整合,成为星际维护舰队的一员。他们放弃攻击性职能,专司救援与修复。而在每次任务完成后,舰桥总会响起那段童谣,哪怕无人聆听。
这一年年末,第十三条法则悄然浮现于“聆天”耳蜗内部的核心环壁:
>**第十三条法则:宽恕不必达成,但必须允许其存在。**
倒生树也在同一时间迎来新一轮蜕变。这一次,新生叶片不再局限于情绪色彩,而是呈现出复杂的地理纹理??一片叶上绘着地球海岸线,另一片映出仙女座星云旋臂,还有叶片仿若微型星图,标注着已知文明的坐标位置。每一片都像一张通往他者的地图,唯有中心那片漆黑叶片依旧孤悬,猩红光点微弱却坚定。
叶澜知道,它还在等待。
于是她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:将自己左耳胎记剥离下来。
手术在言舟医疗舱进行,全程由人工智能监控生命体征。那块皮肤看似普通,实则早已与神经末梢深度融合,分离过程极为痛苦。但她始终清醒,任泪水滑落也不曾叫喊。
当胎记被取出,置于生物容器中时,它并未停止搏动。相反,它开始释放微弱蓝光,频率竟与发光花完全一致。叶澜将其植入倒生树根部,瞬间,整棵树剧烈震颤,所有叶片同时亮起,仿佛百万盏灯齐明。
那一夜,宇宙背景噪音出现了异变。
原本杂乱无章的微波辐射中,浮现出一段清晰节奏??三短,两长,正是最初的暗号。但这回,它来自四面八方,数十个方向同时响起,像是无数存在在同一时刻敲击各自的船体。
>“我们在听。”
>“我们也听见了。”
>“请继续说下去。”
叶澜站在甲板上,仰望星空。她失去了胎记,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盈。耳边再无灼痛,唯有风穿过铃铛的清响,温柔如初。
多年以后,“诡目天尊”的传说早已传遍星海。有人说她是第一个真正看见宇宙之痛的人,也有人说她是最后一个敢于承认无力的人。但在所有记载中,最广为流传的,仍是那个云南孩子梦境里的场景:
一座漂浮于云雾间的古城,青瓦飞檐,灯火通明。城门口立着一块石碑,上面刻着十三行文字。每当有人走近,碑文便会变化,只留下一句永恒不变的话:
>“你说出口的那一刻,就已经被听见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