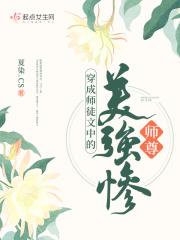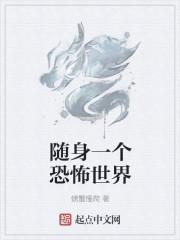笔趣阁>二郎至圣先师 > 333 拼尽全力没能战胜谛听六千字二合一章(第1页)
333 拼尽全力没能战胜谛听六千字二合一章(第1页)
“镇军大将军尽忠职守,实乃三军楷模。”韩松天言道:“但因为当初姜志邦等人从中挑唆,以至于原本忠于朝廷的人马内乱,终究不美。”
郭烈神色如常,表情没有任何变化:“自我从军,由兵卒做起,就只记得六个。。。
雨后的山道泥泞不堪,马蹄踏在湿滑的石板上,溅起一串串浑浊水花。林昭骑在一匹青鬃马上,身后跟着百余名随行者??有背着药箱的老郎中,有扛着木箱的书生,还有几个衣衫粗陋却眼神坚定的农夫。他们自巴蜀出发,已行半月,翻越秦岭时遭遇雪崩,死了三头驮经卷的骡子,也折损了一名年轻匠人。可没人退缩。
“首领,前面就是汉阳镇了。”一名青年策马赶来,是问道者中最年轻的执事李砚,才二十出头,却已在七省跑过义学路线。“据探子回报,此地县令刚被调走,新官未至,正是我们立碑的好时机。”
林昭点头,抬手示意队伍缓行。他望向远处那片依山而建的小镇,炊烟袅袅,鸡犬相闻,看似安宁,可他知道,这平静之下藏着多少无声的苦难。去年一场瘟疫夺去三百条命,无人收尸;前月又有豪强强占良田,逼得一家五口投井。朝廷不管,官府不问,百姓只能跪在破庙里求神明显灵。
“神明若真显灵,也不会等到今天。”林昭低声说。
入镇后,众人悄然分头行动。有人去联络乡老,有人勘察空地准备刻碑,医者则直奔村尾草棚,那里住着几个患肺痨的孩子。林昭独自走向镇中心那座废弃的祠堂,门楣上写着“忠义祠”三字,早已斑驳脱落。他推门进去,灰尘扑面而来,正厅供桌上积满厚灰,唯有中央一块木牌被人擦拭得干干净净,上面墨迹犹新:“此处曾有人教孩子做好人。”
他怔住了。
这是他十年前定下的规矩,从不署名,从不留痕,只为种下一颗种子。可如今,竟有人主动照做,甚至提前为他们铺好了路。
“你来了。”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后堂传来。
林昭转身,只见陈明远缓步走出,鬓角已染霜色,手中仍握着那方旧砚。十年奔波,他的背不再挺直,脚步也有些蹒跚,但眼里的光,比当年更亮。
“你怎么先到了?”林昭问。
“我走的是小路。”陈明远笑了笑,“而且,我不是一个人来的。这半年,‘明德会’已在十八个州扎根,单是义塾就有四百余所。孩子们读《弟子规》,也读《孟子》;郎中治病不收钱,反而倒贴药材;更有不少地方自发组织‘劝善会’,调解邻里纠纷,比衙门还管用。”
林昭缓缓坐下,手指轻抚桌角裂痕:“朝廷呢?”
“密令频发,说是‘严禁私传邪说’,各地都在查抄书籍。上个月,庐州一位老塾师因讲《大学》被杖责三十,活活打死。还有三个义诊点被烧,两名医生失踪。”陈明远声音低沉,“但他们越压,百姓越信。现在很多人说,‘官话说假,问道者讲真’。”
林昭闭目良久,忽而一笑:“你知道北疆老兵们最近在做什么吗?他们在每个村子建‘问道亭’,不是为了拜我,是为了提醒后人:做人不能忘本。有个七岁孩子每天放学都去鞠躬,问他为什么,他说‘因为亭子里住着良心’。”
陈明远动容:“民心如此,大势已成。”
“可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”林昭睁开眼,“当一种信念开始动摇权力根基,掌权者就不会再容忍它只是‘善良’。他们会说它是‘谋逆’,是‘蛊惑人心’。下一步,必然是血洗。”
话音未落,门外传来急促脚步声。李砚冲进来,脸色惨白:“首领!快走!朝廷派兵了!五百铁甲正从洛阳方向疾驰而来,领头的是御前亲军统领赵烈,此人手段狠辣,专司剿灭异党!”
陈明远霍然起身:“不能散!一旦逃窜,十年心血尽毁!百姓会以为我们怕了,信念就会崩塌!”
“我不走。”林昭站起身,走到祠堂门口,望着天边渐暗的云层,“但我们也不硬拼。传令下去,所有经卷立即转移至山中秘洞,义医带着病人先行撤离。至于碑……今晚就刻,明日晨钟响时,必须立起来。”
“可敌人明日午时就到!”李砚焦急。
“那就让他们亲眼看看。”林昭回头,目光如炬,“什么叫‘道在民间’。”
当夜,风雨再起。
数十名工匠冒雨凿石,火把在风中摇曳,映照出一个个专注的脸庞。石碑高六尺,宽三尺,正面刻着八个大字:“**不欺天,不欺民,不欺己良心**。”背面则是《大学》开篇: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”
林昭亲自执锤,一凿一凿,将最后一笔完成。雨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,混着汗水与泥土,滴落在碑文之上,宛如泪痕。
“立碑!”他一声令下。
众人合力将石碑竖起,深埋入土。随后,他们在碑前点燃三支蜡烛,摆上一碗小米粥、一支毛笔、一本手抄《论语》。没有仪式,没有口号,只有沉默的守候。
黎明破晓,第一缕阳光洒在石碑上,字迹清晰如刀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