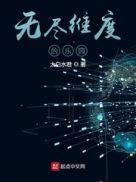笔趣阁>这顶流醉酒发癫,内娱都笑喷了! > 第175章 后悔的芒果卫视(第2页)
第175章 后悔的芒果卫视(第2页)
回到北京一周后,陆钏收到教育部特批文件:《听见塔》将作为全国特殊教育示范项目推广,首批覆盖三百所乡村学校。更令人意外的是,中央广播电视台主动联系,提议制作一档名为《听见中国》的纪实节目,以“声音”为主线,走访全国各地普通人的真实故事。
首站选在怒江傈僳族村寨。拍摄当天,正值雨季初歇。妹妹站在吊桥中央,身后是奔腾江水,面前是一群从未接触过麦克风的孩子。
“你们知道吗?”她轻声说,“我小时候也很怕说话。每次张嘴,都觉得自己声音难听,脑子空白,别人会笑话我。所以我选择了沉默。但后来我发现,真正伤害我的不是说错话,而是没人愿意等我把话说完。”
一个小女孩怯生生举手:“姐姐,那你现在还会紧张吗?”
“当然会。”妹妹笑了,“每次站在这里,我的心跳都快得像要跳出胸口。可我还是来了,因为我知道,总有人正在某个角落,等着听见我的声音。”
镜头转向陆钏。他站在人群外,手里攥着一张纸条??那是昨晚整理素材时,从一台废弃录音机里发现的,字迹模糊:
>“致未来的倾听者:
>我是一个即将失聪的母亲。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再也听不见孩子的笑声。所以,请替我记住:当他喊‘妈妈’时,替我回应;当他哭泣时,替我抱住他。我不怕聋,只怕爱断了声音。”
他闭上眼,深吸一口气。这一刻,他终于理解了“回声”的真正含义??它不只是声音的反弹,更是跨越时间、疾病、死亡的回应之力。
节目播出当晚,收视率破纪录。社交媒体掀起#替我听见#话题风暴,数百万用户上传语音留言,内容五花八门却又惊人一致:都是想对某个人说却始终未能出口的话。
>“爸,我不是不想回家,是我怕你觉得我没出息。”
>“闺蜜,那次你说想考研,我没支持你,是因为我自己也在偷偷准备,怕竞争。对不起。”
>“陌生人,谢谢你那天在地铁站扶了我一把,我没敢道谢,因为我聋了。”
陆钏坐在电脑前一条条听着,直到凌晨。突然,一段匿名音频引起注意。背景音极杂,像是在地下车库,男声沙哑压抑:
>“我是云镜前技术主管林昭。三年前,我主导开发了‘情绪压制算法’,能让公众舆论在72小时内完成逆转。我们用它平息抗议、操控选举、制造偶像……我以为我在掌控时代。直到看到你们的‘声音祭’直播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,我们切断的不是噪音,是人性本身。我现在每天做两件事:一是销毁残留代码,二是去街头帮流浪者录音。他们说的每一句话,我都录下来,存进U盘,标上‘未被统计的生命’。我不知道能不能赎罪,但至少,我想开始听见。”
陆钏听完,久久无言。他点击回复按钮,只写了三个字:“欢迎加入。”
一个月后,“回声工程师联盟”正式成立。成员包括前云镜技术人员、聋哑教育专家、监狱心理咨询师、甚至几位曾因言论获罪的记者。他们的共同信条刻在总部墙上:
>**“我们不再建造控制之塔,我们要修复倾听之路。”**
与此同时,《听见塔》动画正式上线流媒体平台。第一集发布十二小时内,播放量突破八千万。评论区最高赞留言写道:
>“我儿子看完后第一次主动抱了我,说‘爸爸,我其实一直很怕黑’。九年了,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他的真实声音。”
然而,风暴也随之而来。
某权威媒体发表社评《警惕“情感泛滥主义”侵蚀理性社会》,指责“回声计划”煽动情绪、削弱规则意识,呼吁加强监管。紧接着,几家资本巨头联合施压,要求下架相关节目并冻结项目funding。
压力如山压来。投资方接连退出,合作机构纷纷切割关系。就连教育部内部也开始传出“暂缓试点”的风声。
那晚,兄妹俩相对而坐,屋内寂静如渊。
“怎么办?”妹妹问。
陆钏望着窗外霓虹,良久才道:“当年我们在康复中心吃不起药,医生说放弃治疗。我们就自己熬草药,一勺一勺喂。世界从来不会主动给弱者出路,但我们总会想办法凿一条缝。”
第二天,他做出惊人决定??发起“万人共录计划”:邀请所有支持者录制一分钟语音,主题不限,只需真诚讲述一段真实经历。目标:收集一百万条声音,公开上传至去中心化区块链存储系统,永久留存。
消息一出,响应如潮。
学生、工人、快递员、退休教师……无数普通人拿起手机,说出隐藏多年的秘密:
>“我是个同性恋,瞒了父母三十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