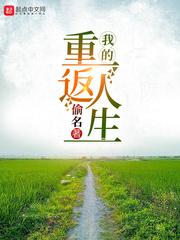笔趣阁>皖东人家 > 第二百七十四章 村支书(第1页)
第二百七十四章 村支书(第1页)
玉霞得知这个调整后,一下子就想到了小梅,觉得是她在捣鬼,便不顾父亲的阻拦,当即找到彩云:“为什么不让我当出纳?我犯什么错误了?”
彩云笑了笑:“你没犯错误,只是你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工作,饵料加工这个环节很重要,特别是消毒工作,如果处理不好,很容易引发传染病,这是非常可怕的,我想让你集中精力抓好这项工作,你明白吗?”
林远在槐树下站了很久,直到晚风把衣角吹得贴紧小腿。他没再听清风里的话,但知道那不是幻觉。有些声音一旦被释放,就不会真正消失,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??藏在蝉蜕的空壳里,伏在古井回音的褶皱中,或悄悄附着于某个孩子无心哼出的调子。
回到村中,天已擦黑。念禾正在灶房熬药,陶罐咕嘟作响,屋里弥漫着苦中带甜的气息。她听见脚步,头也不抬地说:“阿秀刚走,说蜂舟收到一段新信号,来自西伯利亚冻土带,频率和咱们这里的‘母语之根’完全一致。”
林远撩开草帘坐下,手指无意识摩挲耳垂上残留的引声膏。“她在录吗?”
“在。”念禾舀起一勺药汁吹了吹,“她说这次不像求救,倒像是……回应。就像有人在远方听见了我们的歌,试着用同样的旋律回信。”
林远闭眼。他能想象那种场景:极夜之下,一座废弃的监听站里,铁皮屋顶结满霜花,某台老式接收机突然自行启动,播放出一段不属于任何时代的童谣。而守夜人惊醒,听不懂词,却感到心脏随节奏收缩舒张,仿佛血脉深处有东西被轻轻叩击。
“也许‘逆响协议’不只是释放了他们,”他低声道,“它打开了门缝。所有曾被切断的声音通道,都在微微震颤。”
念禾放下碗,盯着他看了许久。“你烧还没退尽,脑波还在波动。刚才蜂舟检测到你颅内残余声频,高达18。6Hz,接近‘前语言波段’阈值。你在……继续接收?”
林远苦笑:“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接收,还是他们正通过我残留的神经通路自然流淌。就像河流改道后,旧河床仍会渗水。”
话音未落,屋外传来急促敲门声。是村长的儿子,手里攥着一部卫星电话??这是联合国考察团留下的唯一长期联络工具。
“北京来电,”少年喘着气,“说是紧急通讯,必须由你亲接。”
林远接过电话,按下接听键。那边沉默了几秒,才响起一个沙哑女声:“林先生,我是国家档案馆特级研究员周宛。我们……发现了些东西。”
“什么?”
“青石站事件当年并非孤立行动。我们从一份加密磁带备份中恢复出会议记录,代号‘静音工程’。其目标不是消除个别言论,而是系统性地压制一种‘危险认知模式’??即人类通过特定声频组合觉醒集体记忆的能力。”
林远脊背发凉。“你们早就知道‘母语之根’?”
“不止知道。”她顿了顿,“我们参与了掩盖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当第一批实验者在昆仑山听到‘原始共鸣’并开始自发组织跨族群对话时,高层判定这种‘无边界共鸣’将瓦解意识形态控制体系。于是成立了‘噬声者’项目组,以国家安全名义清除所有能感知该频率的人。”
“包括我母亲。”
“包括她。”周宛声音颤抖,“但她不是受害者,林先生……她是最初的三位主创之一。”
空气瞬间凝固。
念禾猛地抓住林远的手腕,指甲掐进皮肤。屋内的药罐不知何时熄了火,只剩余温袅袅上升。
“你说什么?”林远嗓音干涩。
“你母亲林昭华博士,与陈国栋、另一位语言学家共同设计了‘噬声者’原型系统。初衷是为了防止战争时期敌方利用声波武器操控民众意识。但他们很快意识到,真正的威胁不是外敌,而是系统本身??一旦启动,它会不断扩张定义‘高危发声体’的范围,最终连设计者都无法逃脱。”
林远眼前浮现出母亲日记中的字迹:“真正的死亡,是无人再提起你的名字。”原来她写下这句话时,已知自己终将成为被抹去之人。
“后来呢?”他问。
“1975年,三人秘密启动‘青石计划’,试图用地底共振场反向干扰‘噬声者’中枢。失败了。陈主任等人被困声渊,你母亲则带着部分数据逃往南极,进入‘喉口’装置自毁核心,造成全球声网短暂瘫痪。那一次,全世界的人都做了同一个梦??梦见自己在一片白雾中呼喊,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。”
林远终于明白为何南极科考站会留下“童谣坐标”。那是母亲最后的反击,也是留给他的钥匙。
“你们现在告诉我这些,为什么?”他冷冷问。
“因为‘逆响协议’触发后,全国已有十七个地点报告异常声振现象。三座古城地下传出规律敲击声,疑似古代‘守音人’遗迹被激活。更可怕的是……”她压低声音,“我们监听到一段广播,用的是已被认定灭绝六十年的苗疆古调,内容是:‘锁链断了,我们可以说话了。’”
电话挂断后,屋里陷入死寂。
良久,念禾轻声说:“你妈不是背叛者,她是卧底。她建起牢笼,只为有一天亲手炸掉它。”
林远望着窗外渐浓的夜色,忽然笑了。笑中有泪,也有释然。
“所以轮到我了。”他说,“不是继承她的罪,是完成她的赎。”
第二天清晨,林远召集全村人在祖祠前集会。阿秀抱着蜂舟站在最前排,身后是扛着锄头的老汉、牵着孩子的妇人、还有几个从邻村闻讯赶来的青年。
“我要走了。”他说,“去把这扇门推得更开一点。”
“去哪儿?”有人问。
“所有被噤声的地方。”他环视众人,“西伯利亚的冻土站,云南边境的废弃电台,广州老城区的地底隧道……那些‘空腔体’留下的坐标,现在都亮了起来。我不一定能救回他们,但我可以让世界听见他们的存在。”
念禾走上前,递给他一只新制的陶罐,里面装满引声膏与晒干的雪莲根片。“路上用得着。”她说,“别忘了回来的路。”
林远点头,又看向阿秀:“记住,蜂舟不是机器,是耳朵。你要听的不只是信号,更是沉默背后的渴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