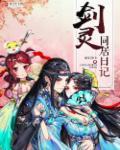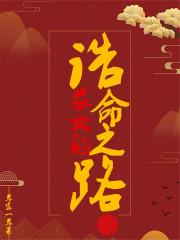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全家夺我军功,重生嫡女屠了满门 > 第684章 王爷追问 除了本王你还要谁(第1页)
第684章 王爷追问 除了本王你还要谁(第1页)
待乐平川写完,许靖央拿起来瞧了两眼。
她知道乐平川没胆子骗她,都已经是这个时候了,皇帝将他当做棋子,已是走到绝路,所以他只能选择她这棵大树,祈求庇护。
许靖央吩咐黑衣人:“由你负责,安顿乐老先生一家,务必稳妥。”
“是!”
乐平川小心翼翼问:“王爷,如果那四名押送草民的官吏醒来,发现我们逃跑无踪,若向上禀奏,草民和草民的家人后代,岂不都成了官府通缉的逃犯……”
许靖央折起纸张放入袖中,漆黑凤眸看向他。。。。。。
夜风穿廊,吹动唤名塔檐下铜铃,叮咚作响,如低语回荡。苏清越伫立塔顶,手中贝壳微光流转,映得她眼底清澈而坚定。远处昆仑山峦起伏,晨雾缭绕,仿佛天地初开时的混沌未分。她闭目深吸一口气,将那枚新制的贝壳轻轻系于腰间??它不再只是唤醒亡魂的信物,而是千万人心中不灭记忆的象征。
自清虚观一役已过三月,朝堂震荡渐平,但暗流从未止息。陆明漪虽被囚于地牢,其“静养局”残党却如影随形,在各州府悄然渗透。太医院中多名医官以“疗愈心疾”为名,秘密推行一种名为“安神散”的药方,服用者皆出现短暂失忆、情绪淡漠之症。幸得沈知微察觉异常,从药渣中提取出微量愿核粉尘,才揭穿此乃新型记忆压制手段。
朝廷震怒,下令彻查。然主审官员刚上任七日,便突患“风疾”,言语错乱,竟连自家妻儿亦不相识。案卷一夜之间尽数焚毁,仅余一角焦纸飘落御史台门槛,上书二字:“慎言。”
苏清越读罢,冷笑一声,命人将残纸裱起,悬于四明堂正厅,与《备忘录十三条》并列高挂。她当众宣布:“自此日起,铭名院学生若发现任何疑似抹名行为,无论涉及何人,皆可直奏陛下,不受层级所限。”此举震动百官,民间称颂为“开口令”。
然而,真正的风暴,始于一场婚礼。
林小满考入铭名院次年,以优异成绩通过初试,成为寻名司最年轻的见习使。她主理的第一桩案件,是挖掘南宋一位女书院山长的事迹。据地方志残本记载,此人曾主持编纂《女学通义》,倡导女子入学、参政、立业,后因触怒权贵,全书被焚,本人亦遭流放岭南,死于途中。林小满循迹南下,历时两月,终在福建一座破庙墙缝中寻得半卷手稿,字迹斑驳却仍可辨识。
正当她准备返程之际,却收到家中急信:其妹林小柔,已被许配给户部尚书之子为妾。
消息传来,苏清越拍案而起。林家虽改姓沈氏,世代务农,但从林晚照那一脉传下的精神早已根植血脉。林小柔自幼聪慧,熟读史书,曾在村塾代课授学,深受乡邻敬重。如今竟要屈身为妾,实为羞辱。
更令人愤慨的是,婚事由当地县令亲自促成,理由竟是“女子读书过多易生妄念,宜早嫁以正心性”。而户部尚书之子素有劣迹,强抢民女、酗酒殴仆,早已声名狼藉。
苏清越当即修书一封,遣快马送往台州,劝林家拒婚。然三日后回报,林父已被县衙拘押,罪名是“抗旨不遵”,而林小柔则被软禁家中,门窗钉死,不得外出。
百姓哗然。
翌日清晨,四明堂门前聚集数百民众,多为乡野妇孺,手持紫茉莉花束,跪地请愿。她们中有教女儿识字的老妪,有偷偷抄录《铭心录》的村妇,也有曾因言获罪的女吏。一人领头高呼:“还我林小柔!护我读书权!”声音悲怆,响彻云霄。
苏清越立于台阶之上,望着眼前黑压压的人群,心中翻涌如潮。她忽然明白,这已非一人一家之冤,而是所有曾被压制、被剥夺话语权的女子共同发出的呐喊。
她转身走入堂内,取来一面铜鼓,置于门前高台。
三声鼓响,惊飞檐上寒鸦。
“今日,我不以铭名院掌令身份说话,”她的声音清越如刃,穿透晨雾,“我以一名女子的身份宣告:林小柔,不该为妾!天下女子,皆不该因识字而受罚!”
人群沸腾。
她随即写下《请废女子禁学令疏》,列举历代才女功绩,痛陈禁学之弊,并附上百余名受害女子联名血书,派陈砚舟连夜送入宫中。
皇帝览奏良久,未置可否。倒是皇后召见苏清越,于凤仪殿密谈两个时辰。次日,一道谕旨颁下:林小柔婚事暂缓,交由礼部重新审议;全国范围内暂停一切强迫女子辍学、禁读之举;凡因言论被贬黜的女官,可申请复职审查。
举国震动,欢呼雷动。
可就在此时,京城忽传噩耗:林小满在归途遇袭,座船沉没于钱塘江口,尸骨无存。
苏清越闻讯,如遭雷击。她不信林小满会死得如此轻易。那孩子坚韧聪慧,行事缜密,怎会在众目睽睽之下遭人暗算而不留痕迹?她亲赴江岸勘察,却发现事发水域并无激流漩涡,船只残骸亦过于完整,似人为沉放。
更蹊跷的是,数日后,一名渔夫在芦苇荡深处捞起一只木匣,内藏一本日记,字迹确系林小满亲笔。其中最后一页写道:
>“若我失踪,请勿哀悼。真相藏在‘静音井’之下。那里有她们的声音,也有我们的未来。”
苏清越心头剧震。“静音井”三字,她曾在净忆堂古籍中见过??那是前朝专门用来囚禁“多言妇”的地下牢窟,犯人被锁于井底石室,终生日不能语,唯余耳听外界之声,却无法回应。传说井壁刻满被删改的历史,每一寸都浸透血泪。
而据残卷记载,静音井共有七口,分布于七座古都,最后一口,就在京都西郊荒园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