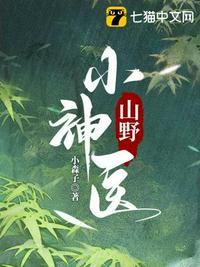笔趣阁>斗罗:日月当空,当天命所归! > 第二百九十二章 落幕(第1页)
第二百九十二章 落幕(第1页)
空虚战场的局势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一点点地倒向了元初神界。
而在虚空战场的一角,仍旧是那么地平静和谐。
天马江桦微笑着串起一条条鱼在火架上烤,小舞机械地重复着循环的动作,而唐舞桐则是吃下一条。。。
晨光初透,海面如镜。星火号静静停泊在珊瑚湾外,船体倒映着天边渐次铺展的金红朝霞。陆明站在甲板边缘,赤足踩在微凉的金属板上,呼吸随着潮汐起伏。他的双眼依旧无光,但眉宇间却有种难以言喻的清明,仿佛能看见比常人更深的东西??不是形影,而是心绪的涟漪。
“他们来了。”他忽然说。
周念安正翻阅一份加密档案,闻言抬头:“谁?”
“那些还没醒的人。”陆明轻声道,“他们的梦还在路上,像迷途的鸟,找不到归巢的方向。”
话音未落,舱内警报轻微震动。愿图网络终端自动开启,投影出一组动态数据流:全球范围内,仍有约四千七百万个潜在共情节点处于沉寂状态,集中在战乱、贫困与信息封锁区域。这些地方的孩子从未听过“共梦计划”的讯息,老人不识字,难民营地连电力都时有时无。善意的波纹未曾抵达他们,如同阳光照不到深谷。
陈怀远的声音从通讯器中传来:“我们唤醒了银河亭台,可并非所有人都听见钟声。”
周念安攥紧拳头:“那怎么办?再发一次信号?用卫星广播覆盖?”
“不行。”陆明摇头,“真正的共鸣不能靠强迫传播。它必须自发,必须出自‘我想帮’,而不是‘我被要求帮’。否则,哪怕亿万次善举叠加,也只是空壳。”
沉默片刻,周念安忽然起身:“我去南线。”
“你一个人?”陈怀远惊问。
“不,是和他们一起去。”她指向休息室??那里,三十六名愿种营少年已整装待发,每人胸前挂着贝壳吊坠,眼神坚定。
“我们要去最暗的地方。”她说,“不是送物资,也不是宣讲理念。只是存在。只是做一件事:让一个陌生人觉得,这世界还不算太冷。”
三天后,第一支“微光小队”降落在非洲东部某难民营外围。这里曾因水源争夺爆发过多次冲突,如今只剩破旧帐篷与疲惫面孔。孩子们眼神麻木,妇女低头行走,连哭泣都显得奢侈。
队伍没有穿制服,也没有携带任何标识。他们只是走进去,像偶然路过的人。
第一个行动很简单:一名女孩蹲下,为一个满脚泥泞的小男孩清洗伤口,用的是自己仅有的半瓶饮用水。她不说一句话,只是轻轻吹了吹他的脚背,像母亲那样。
男孩愣住,然后哭了。
这一幕被远处一位老妇看见。她默默转身,回帐篷拿出一块干饼,塞进女孩手里。
当晚,第二件事发生:两名队员合力搭起一座简易书架,摆上带来的图画本和铅笔。起初无人靠近,直到一个小女孩试探性地画了一朵花??歪歪扭扭,却鲜艳得刺眼。
“这是白梅吗?”她问。
“你想它是,就是。”男孩回答。
她笑了。那一瞬间,营地监控系统捕捉到一次微弱的Y级脉冲波动,虽不及峰值千分之一,但它确实存在,且持续扩散。
与此同时,在中东某地下避难所,另一支小队正经历完全不同的情境。战火未歇,墙体震颤。一名队员抱着录音机坐在角落,反复播放一段声音??那是十年前周振华医生在战地医院的最后一段讲课录音,关于如何在无药可用时稳定伤员情绪。
“记住,恐惧会传染,但平静也是。”他说。
几个小时后,一名原本暴躁的伤兵渐渐安静下来。他睁开眼,看着身边瑟瑟发抖的年轻人,竟伸手拍了拍对方肩膀:“别怕,我会护着你。”
那一刻,墙缝中的苔藓突然抽出嫩绿新芽。
而在南美洲雨林深处,第三支小队跋涉数日,终于找到那位曾以血试毒的土著少女。她如今已是部落医者,听闻来意后沉默良久,最终取出一株罕见草药,交给陆明派来的联络员。
“这不是药。”她说,“这是记忆。每一代人都要尝一次它的苦,才知道什么叫‘值得救’。”
联络员含泪接过,将草药封入特制胶囊,贴上标签:“承愿?源点03”。
当夜,联合国圣殿内的愿舟内部光影再度变化。新增的画面里,有非洲孩子递出的第一杯水,有中东母亲为敌对阵营婴儿哺乳的瞬间,有雨林祭坛上燃烧的古老咒文……每一帧都被水晶船体吸收,转化为更深层的共振频率。
然而,黑暗并未彻底退去。
某夜,周念安在临时营地收到一封奇怪包裹。没有寄件人,只有一块黑色晶体,表面刻着断裂钥匙插进冰心的符号。她刚触碰,耳边便响起低语:
>“你们点燃灯火,我们就藏进影子里。
>你们拥抱彼此,我们就教会孤独生长。